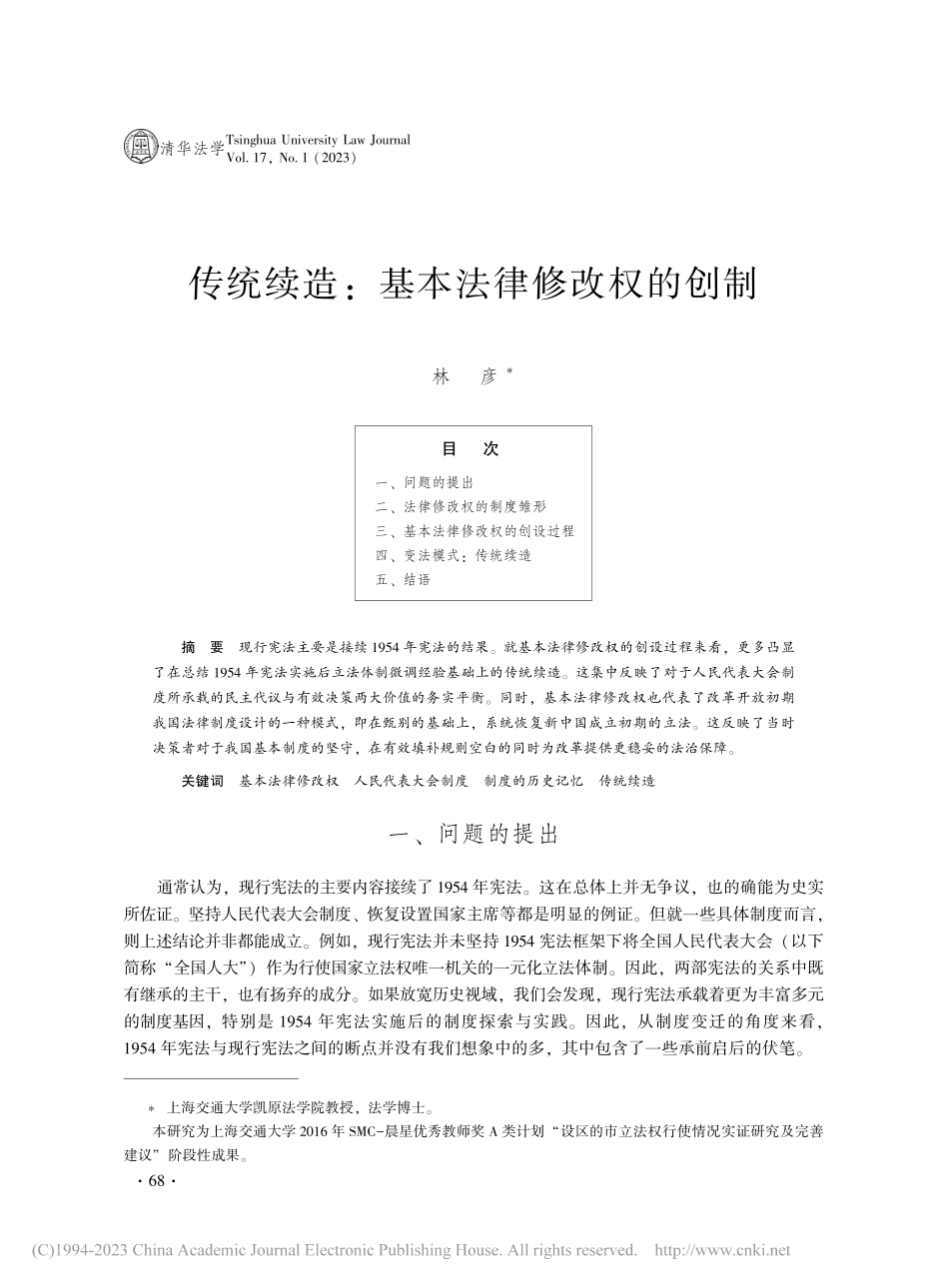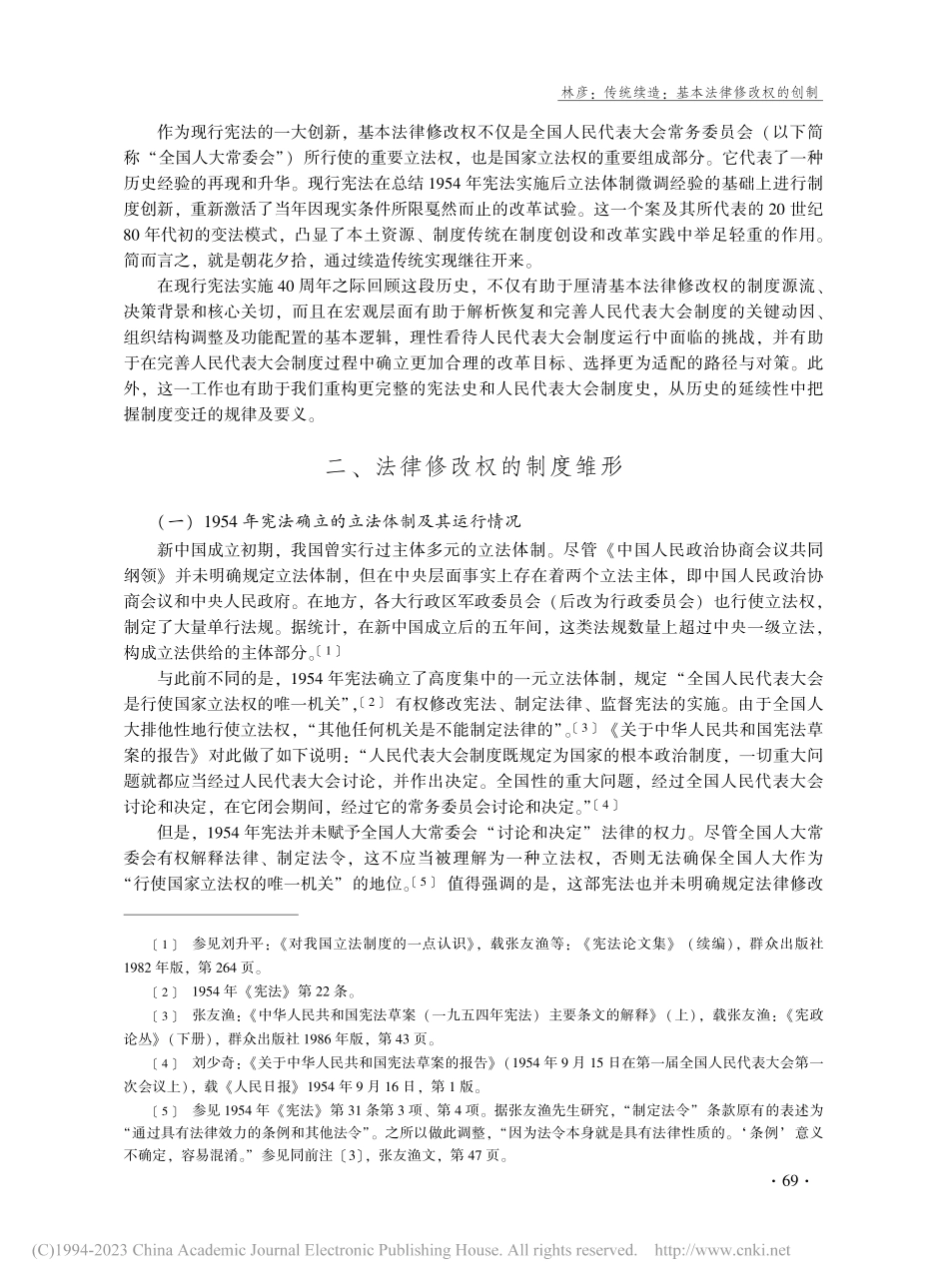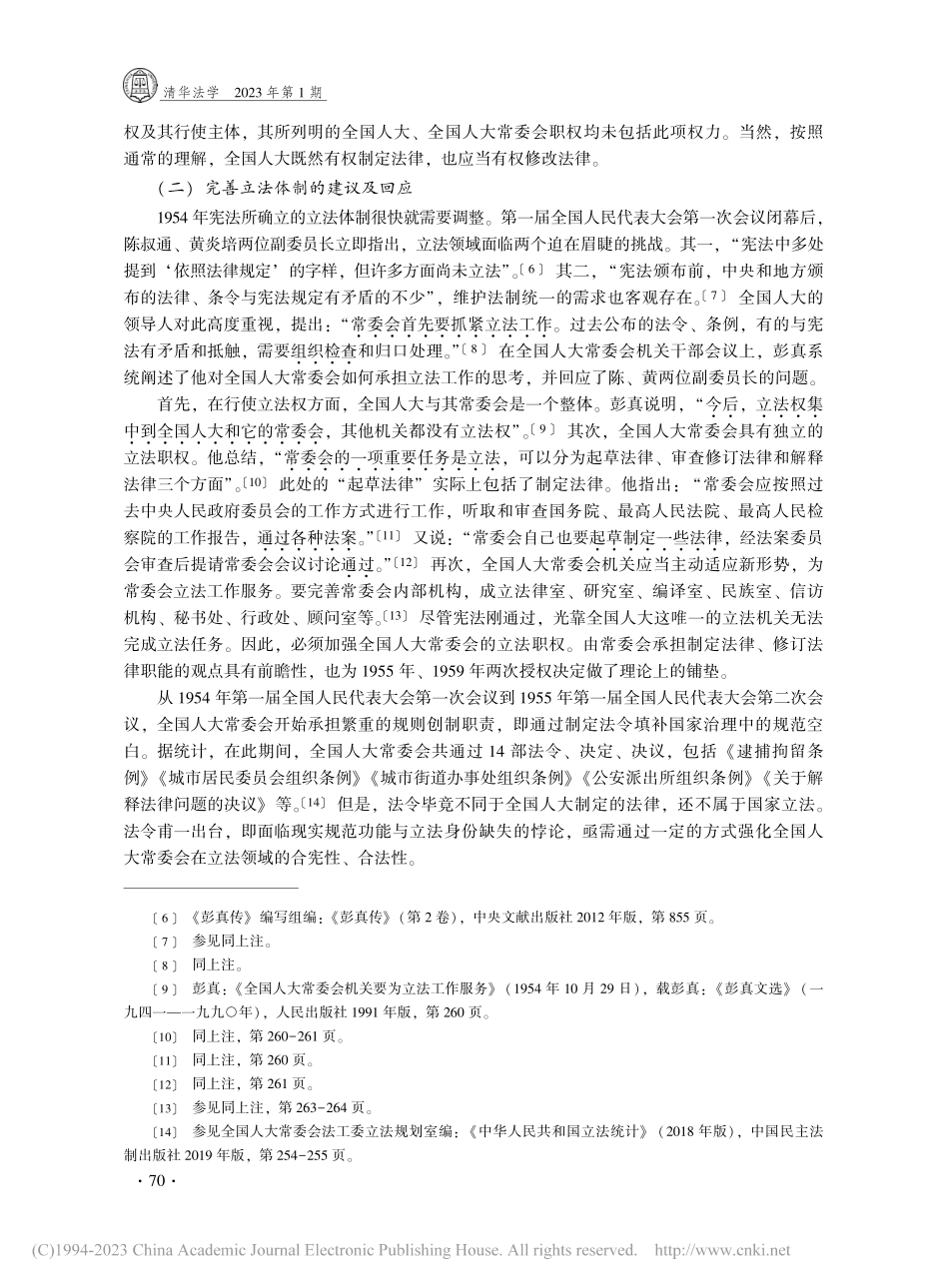清华法学TsinghuaUniversityLawJournalVol.17,No.1(2023)传统续造: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创制林彦∗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法律修改权的制度雏形三、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创设过程四、变法模式:传统续造五、结语摘要现行宪法主要是接续1954年宪法的结果。就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创设过程来看,更多凸显了在总结1954年宪法实施后立法体制微调经验基础上的传统续造。这集中反映了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承载的民主代议与有效决策两大价值的务实平衡。同时,基本法律修改权也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法律制度设计的一种模式,即在甄别的基础上,系统恢复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立法。这反映了当时决策者对于我国基本制度的坚守,在有效填补规则空白的同时为改革提供更稳妥的法治保障。关键词基本法律修改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度的历史记忆传统续造一、问题的提出通常认为,现行宪法的主要内容接续了1954年宪法。这在总体上并无争议,也的确能为史实所佐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恢复设置国家主席等都是明显的例证。但就一些具体制度而言,则上述结论并非都能成立。例如,现行宪法并未坚持1954宪法框架下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唯一机关的一元化立法体制。因此,两部宪法的关系中既有继承的主干,也有扬弃的成分。如果放宽历史视域,我们会发现,现行宪法承载着更为丰富多元的制度基因,特别是1954年宪法实施后的制度探索与实践。因此,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1954年宪法与现行宪法之间的断点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多,其中包含了一些承前启后的伏笔。·86·∗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研究为上海交通大学2016年SMC-晨星优秀教师奖A类计划“设区的市立法权行使情况实证研究及完善建议”阶段性成果。作为现行宪法的一大创新,基本法律修改权不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所行使的重要立法权,也是国家立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代表了一种历史经验的再现和升华。现行宪法在总结1954年宪法实施后立法体制微调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重新激活了当年因现实条件所限戛然而止的改革试验。这一个案及其所代表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变法模式,凸显了本土资源、制度传统在制度创设和改革实践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简而言之,就是朝花夕拾,通过续造传统实现继往开来。在现行宪法实施4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厘清基本法律修改权的制度源流、决策背景和核心关切,而且在宏观层面有助于解析恢复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