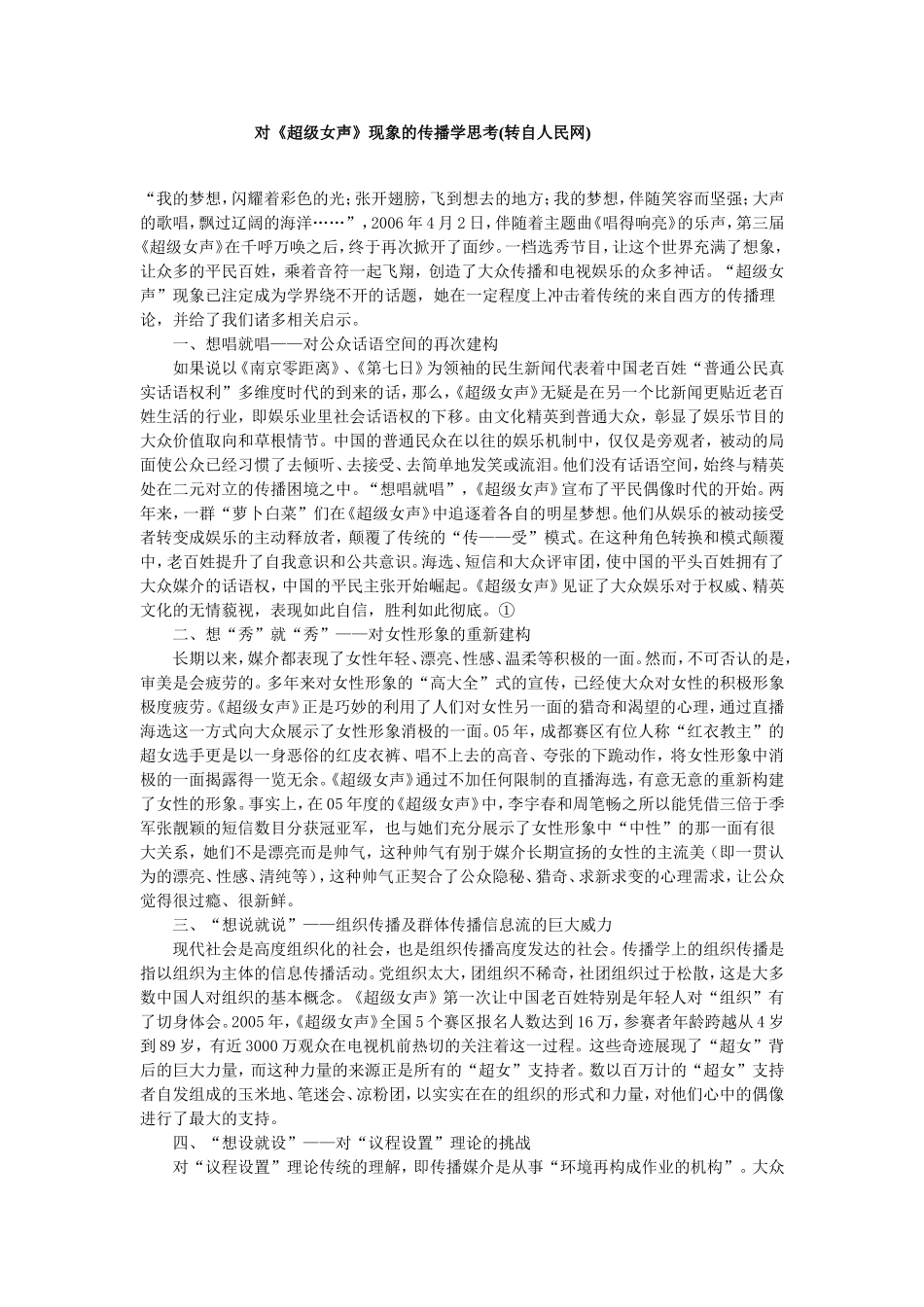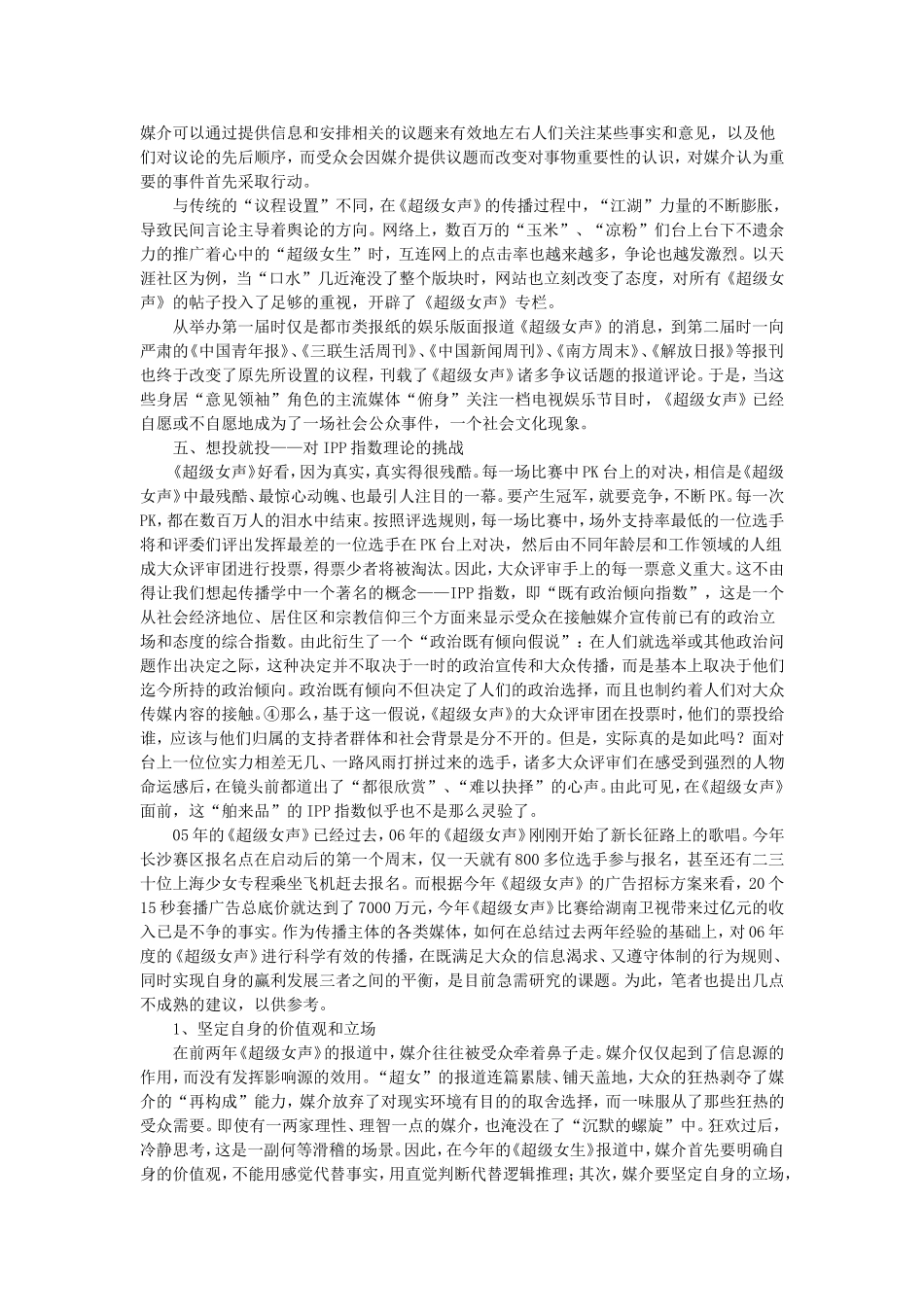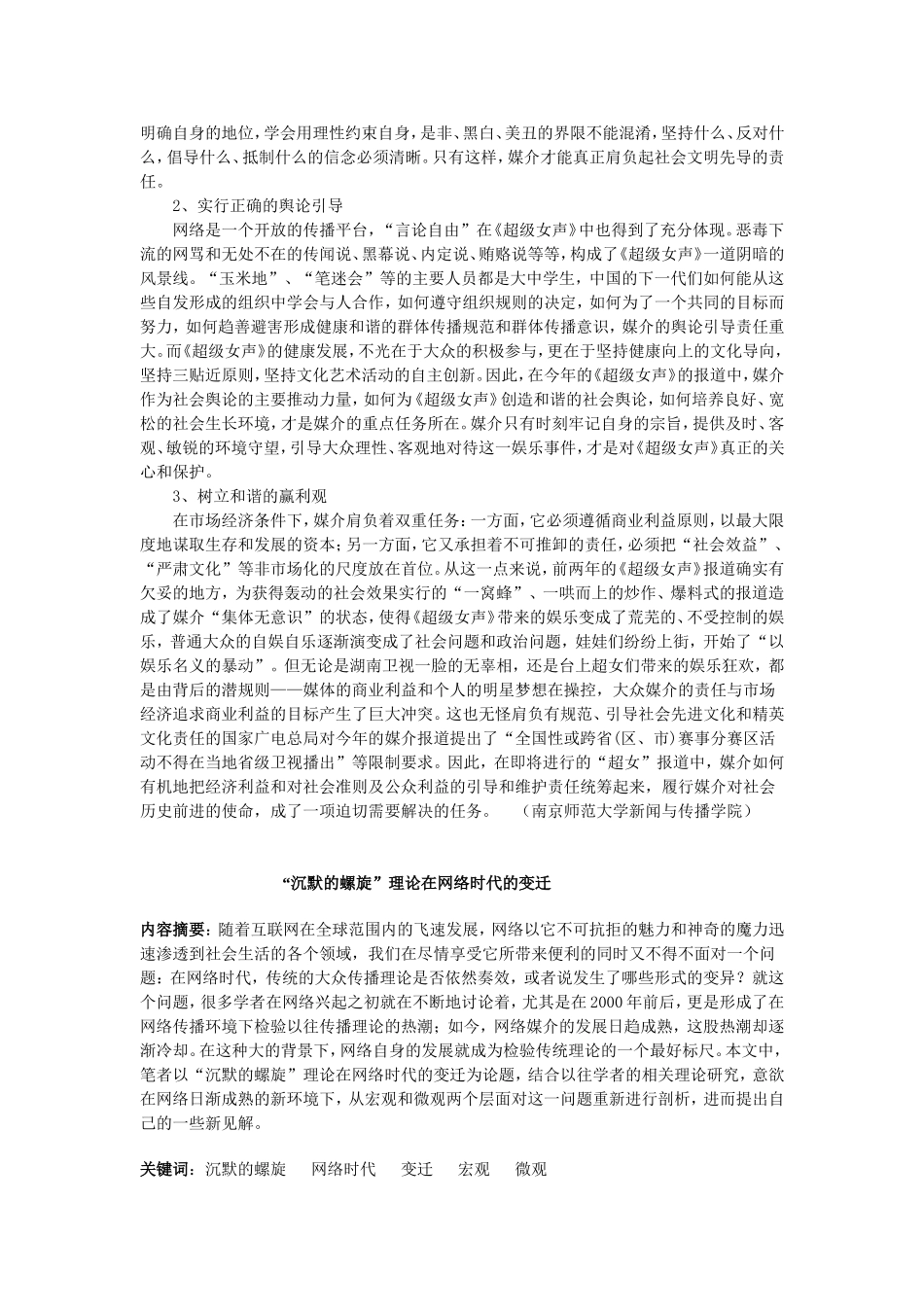对《超级女声》现象的传播学思考(转自人民网)“我的梦想,闪耀着彩色的光;张开翅膀,飞到想去的地方;我的梦想,伴随笑容而坚强;大声的歌唱,飘过辽阔的海洋……”,2006年4月2日,伴随着主题曲《唱得响亮》的乐声,第三届《超级女声》在千呼万唤之后,终于再次掀开了面纱。一档选秀节目,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想象,让众多的平民百姓,乘着音符一起飞翔,创造了大众传播和电视娱乐的众多神话。“超级女声”现象已注定成为学界绕不开的话题,她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来自西方的传播理论,并给了我们诸多相关启示。一、想唱就唱——对公众话语空间的再次建构如果说以《南京零距离》、《第七日》为领袖的民生新闻代表着中国老百姓“普通公民真实话语权利”多维度时代的到来的话,那么,《超级女声》无疑是在另一个比新闻更贴近老百姓生活的行业,即娱乐业里社会话语权的下移。由文化精英到普通大众,彰显了娱乐节目的大众价值取向和草根情节。中国的普通民众在以往的娱乐机制中,仅仅是旁观者,被动的局面使公众已经习惯了去倾听、去接受、去简单地发笑或流泪。他们没有话语空间,始终与精英处在二元对立的传播困境之中。“想唱就唱”,《超级女声》宣布了平民偶像时代的开始。两年来,一群“萝卜白菜”们在《超级女声》中追逐着各自的明星梦想。他们从娱乐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娱乐的主动释放者,颠覆了传统的“传——受”模式。在这种角色转换和模式颠覆中,老百姓提升了自我意识和公共意识。海选、短信和大众评审团,使中国的平头百姓拥有了大众媒介的话语权,中国的平民主张开始崛起。《超级女声》见证了大众娱乐对于权威、精英文化的无情藐视,表现如此自信,胜利如此彻底。①二、想“秀”就“秀”——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建构长期以来,媒介都表现了女性年轻、漂亮、性感、温柔等积极的一面。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审美是会疲劳的。多年来对女性形象的“高大全”式的宣传,已经使大众对女性的积极形象极度疲劳。《超级女声》正是巧妙的利用了人们对女性另一面的猎奇和渴望的心理,通过直播海选这一方式向大众展示了女性形象消极的一面。05年,成都赛区有位人称“红衣教主”的超女选手更是以一身恶俗的红皮衣裤、唱不上去的高音、夸张的下跪动作,将女性形象中消极的一面揭露得一览无余。《超级女声》通过不加任何限制的直播海选,有意无意的重新构建了女性的形象。事实上,在05年度的《超级女声》中,李宇春和周笔畅之所以能凭借三倍于季军张靓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