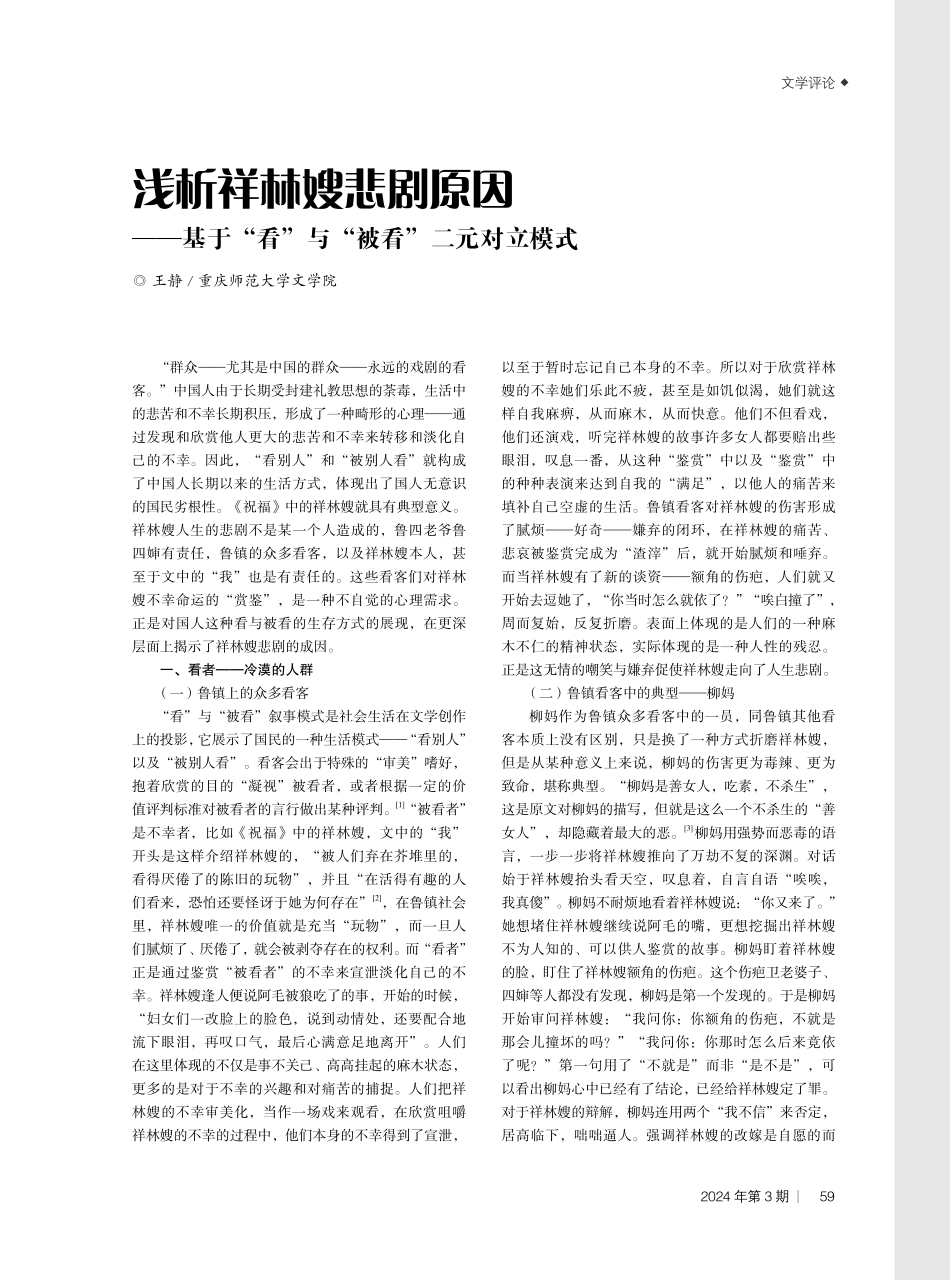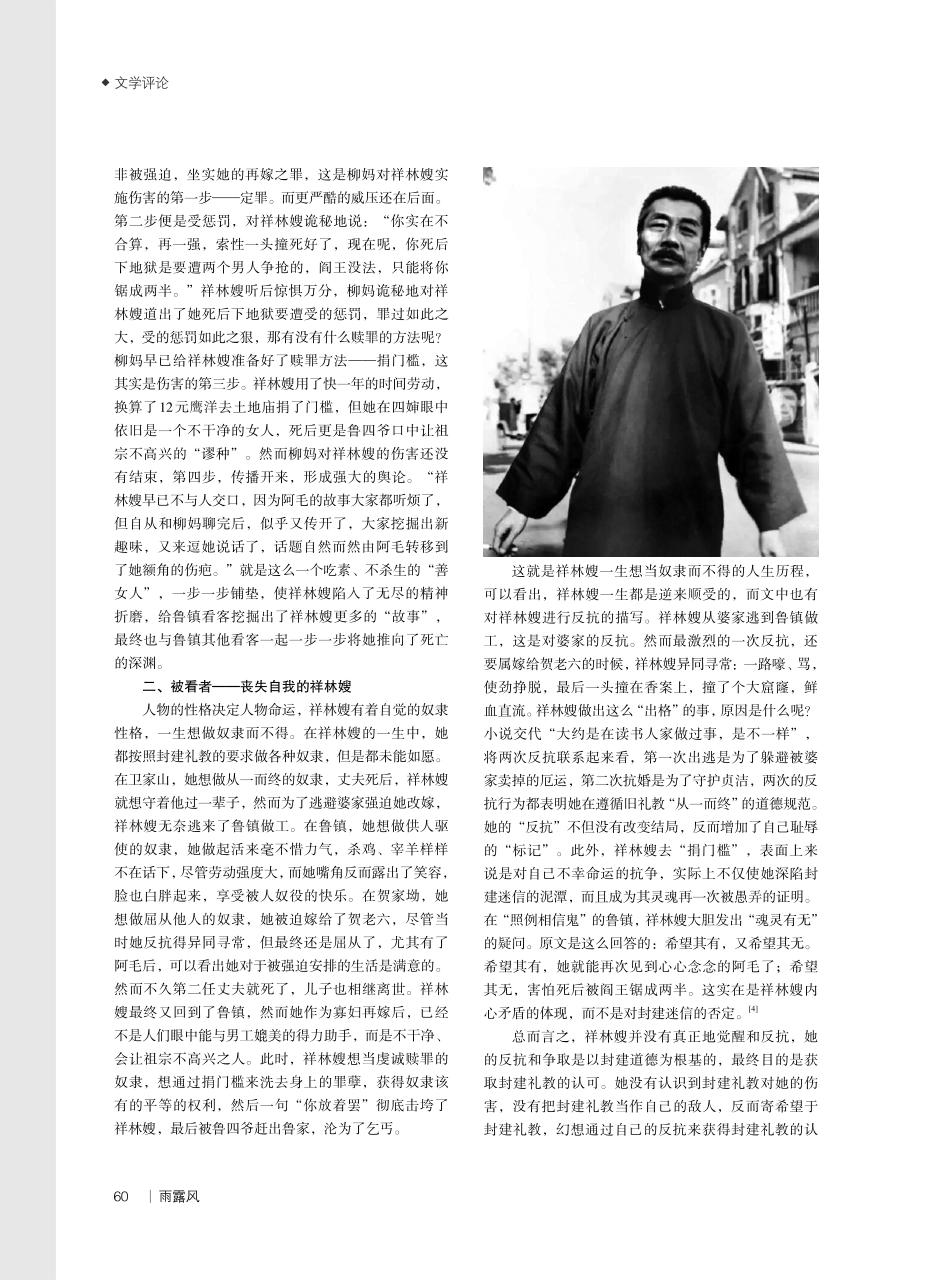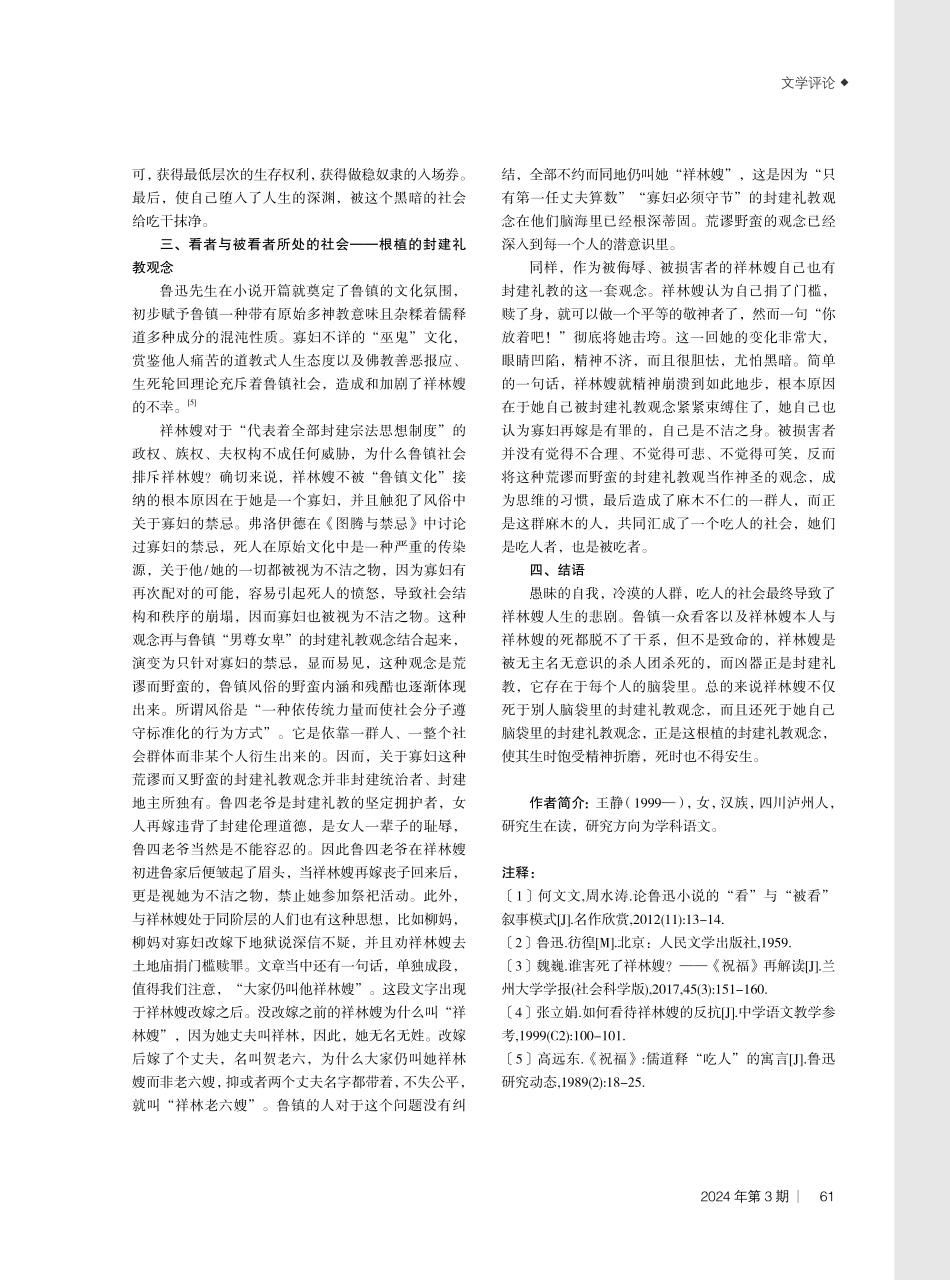592024年第3期文学评论◆“群众——尤其是中国的群众——永远的戏剧的看客。”中国人由于长期受封建礼教思想的荼毒,生活中的悲苦和不幸长期积压,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心理——通过发现和欣赏他人更大的悲苦和不幸来转移和淡化自己的不幸。因此,“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就构成了中国人长期以来的生活方式,体现出了国人无意识的国民劣根性。《祝福》中的祥林嫂就具有典型意义。祥林嫂人生的悲剧不是某一个人造成的,鲁四老爷鲁四婶有责任,鲁镇的众多看客,以及祥林嫂本人,甚至于文中的“我”也是有责任的。这些看客们对祥林嫂不幸命运的“赏鉴”,是一种不自觉的心理需求。正是对国人这种看与被看的生存方式的展现,在更深层面上揭示了祥林嫂悲剧的成因。一、看者——冷漠的人群(一)鲁镇上的众多看客“看”与“被看”叙事模式是社会生活在文学创作上的投影,它展示了国民的一种生活模式——“看别人”以及“被别人看”。看客会出于特殊的“审美”嗜好,抱着欣赏的目的“凝视”被看者,或者根据一定的价值评判标准对被看者的言行做出某种评判。[1]“被看者”是不幸者,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文中的“我”开头是这样介绍祥林嫂的,“被人们弃在芥堆里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并且“在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还要怪讶于她为何存在”[2],在鲁镇社会里,祥林嫂唯一的价值就是充当“玩物”,而一旦人们腻烦了、厌倦了,就会被剥夺存在的权利。而“看者”正是通过鉴赏“被看者”的不幸来宣泄淡化自己的不幸。祥林嫂逢人便说阿毛被狼吃了的事,开始的时候,“妇女们一改脸上的脸色,说到动情处,还要配合地流下眼泪,再叹口气,最后心满意足地离开”。人们在这里体现的不仅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状态,更多的是对于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捕捉。人们把祥林嫂的不幸审美化,当作一场戏来观看,在欣赏咀嚼祥林嫂的不幸的过程中,他们本身的不幸得到了宣泄,以至于暂时忘记自己本身的不幸。所以对于欣赏祥林嫂的不幸她们乐此不疲,甚至是如饥似渴,她们就这样自我麻痹,从而麻木,从而快意。他们不但看戏,他们还演戏,听完祥林嫂的故事许多女人都要赔出些眼泪,叹息一番,从这种“鉴赏”中以及“鉴赏”中的种种表演来达到自我的“满足”,以他人的痛苦来填补自己空虚的生活。鲁镇看客对祥林嫂的伤害形成了腻烦——好奇——嫌弃的闭环,在祥林嫂的痛苦、悲哀被鉴赏完成为“渣滓”后,就开始腻烦和唾弃。而当祥林嫂有了新的谈资——额角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