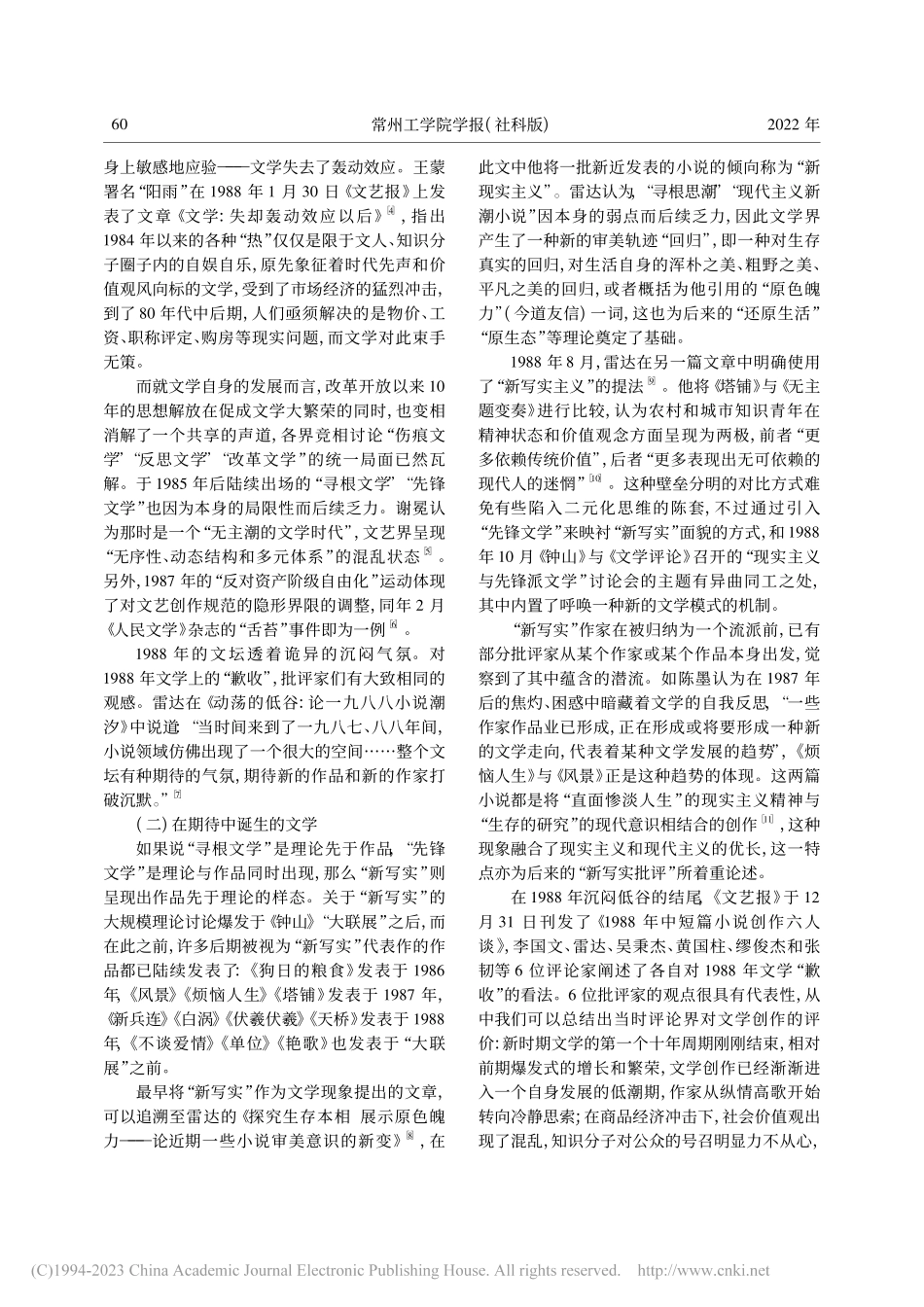第40卷第6期2022年12月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JournalofChangzhouInstitute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Edition)Vol.40No.6Dec.2022doi:10.3969/j.issn.1673-0887.2022.06.012收稿日期:20220910作者简介:周昱均(1995—),女,广东东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从野蛮生长到有序运作———论“新写实”之发生周昱均(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新写实”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折期重要的文学现象,实际上也是一场成功的文学策划运动,《钟山》杂志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写实”的发展走向及其在文学史中的面貌。“新写实”从未经专门扶持的野蛮生长状态,到被刊物的有序运作所“驯化”,这一过程体现了转型时代微妙而复杂的社会潜流,亦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生产的一个难得样本。关键词:“新写实”;《钟山》;文学生产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0887(2022)06-0059-05“新写实”诞生于文坛较为“低迷”的1987年,它生长于“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的疲软困境和批评家对一种新的文学模式的期待之中,经过《钟山》杂志的大力倡导,“新写实”被视作现实主义的隔代后裔,成了拯救文坛于尴尬之中的救命稻草。然而,嗡鸣的批评话语命名并建构了“新写实”,但也一定程度遮蔽了具体的历史细节,“新写实”便以简化或者说变形的面貌进入文学史的叙述。因此,呈现并解析《钟山》介入之前孕育新写实小说的时代与社会土壤,以及“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以下简称“大联展”)对“新写实”后续发展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新写实”具体的历史面貌。正如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所说,“历史通过从时间顺序表里编出故事的成功正是历史阐释效用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编织情节”的运作[1]。这种编织与小说的“虚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二者都是通过压制或抬高一些因素、塑造人物个性、重复某些主题、选择性地描写、变化声音和视点等等,来讲述一个“故事”。因此,当我们理解并接受某种历史叙述时,应当始终保持警惕,即它不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而是一种对已发生事件之间的因果逻辑的处理方式。一、成为“新写实”之前(一)动荡的浪潮与沉闷的低谷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改革开放”振臂高呼的人们开始感受到了社会剧变带来的阵痛: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零售物价平均每年上涨7.4%,1988年更是全年上涨18.5%[2]。物价的疯狂上涨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