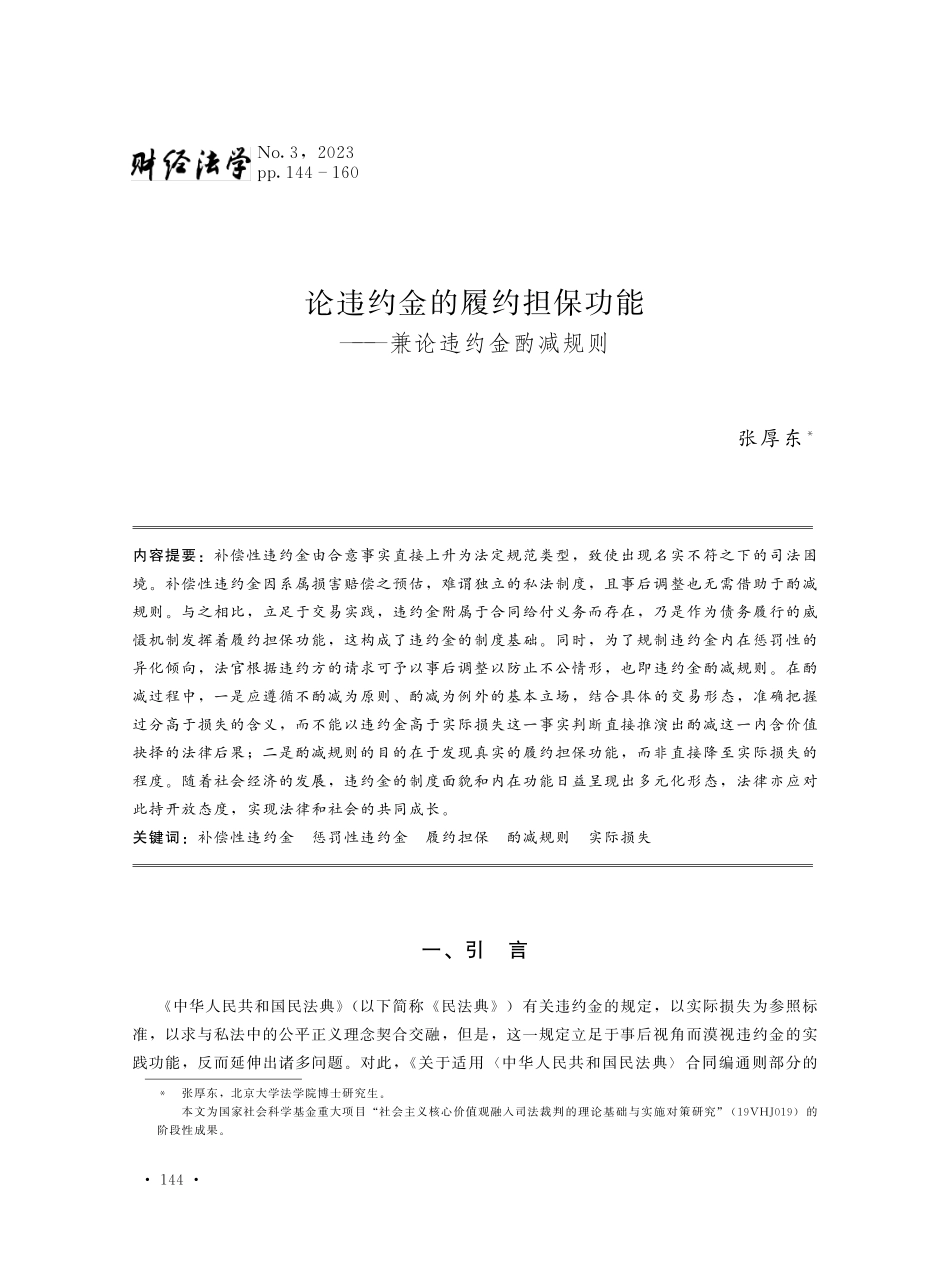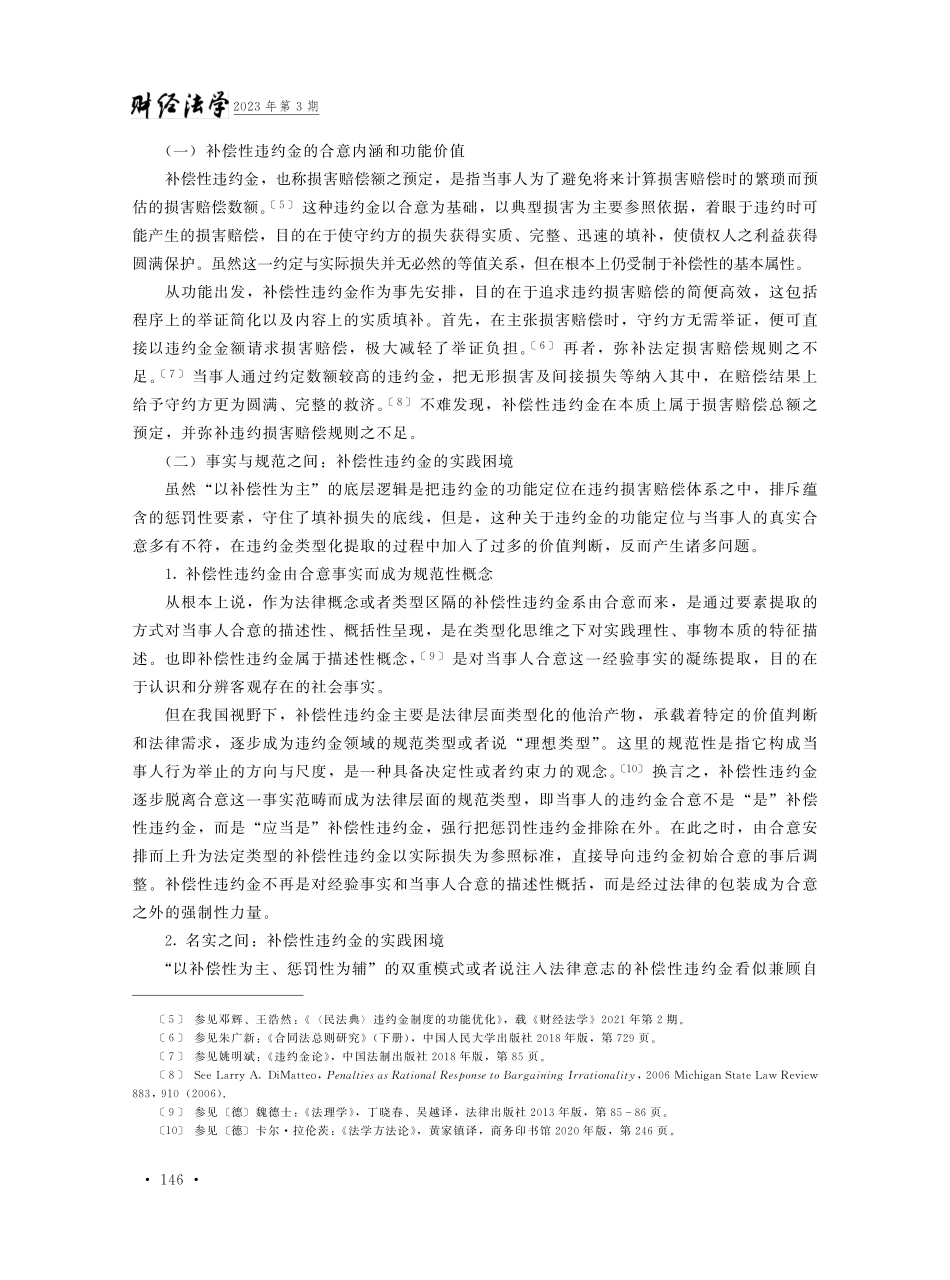*张厚东,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司法裁判的理论基础与实施对策研究”(19VHJ019)的阶段性成果。No.3,2023pp.144160论违约金的履约担保功能———兼论违约金酌减规则张厚东*内容提要:补偿性违约金由合意事实直接上升为法定规范类型,致使出现名实不符之下的司法困境。补偿性违约金因系属损害赔偿之预估,难谓独立的私法制度,且事后调整也无需借助于酌减规则。与之相比,立足于交易实践,违约金附属于合同给付义务而存在,乃是作为债务履行的威慑机制发挥着履约担保功能,这构成了违约金的制度基础。同时,为了规制违约金内在惩罚性的异化倾向,法官根据违约方的请求可予以事后调整以防止不公情形,也即违约金酌减规则。在酌减过程中,一是应遵循不酌减为原则、酌减为例外的基本立场,结合具体的交易形态,准确把握过分高于损失的含义,而不能以违约金高于实际损失这一事实判断直接推演出酌减这一内含价值抉择的法律后果;二是酌减规则的目的在于发现真实的履约担保功能,而非直接降至实际损失的程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违约金的制度面貌和内在功能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形态,法律亦应对此持开放态度,实现法律和社会的共同成长。关键词:补偿性违约金惩罚性违约金履约担保酌减规则实际损失一、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有关违约金的规定,以实际损失为参照标准,以求与私法中的公平正义理念契合交融,但是,这一规定立足于事后视角而漠视违约金的实践功能,反而延伸出诸多问题。对此,《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441·张厚东:论违约金的履约担保功能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合同编通则解释(征求意见稿)》)专列三条就违约金的事后调整,尤其是针对酌减事宜予以详细规定。通常而言,凡对意思自治作出限制者,须基于特定目的并承担相应的论证负担。〔1〕与之同理,违约金作为合意产物,事后酌减应为原则之例外。反观司法实践,酌减规则轻易突破当事人的初始合意,呈现出泛化趋势而未受到目的性及妥适性之检视。对此,当事人不得不另行安排以控制酌减泛化的负面效应,或以特约排除酌减规则的适用,〔2〕或通过约定虚高的违约金以规避酌减规则。〔3〕究其原因,乃是司法机关把具有高度抽象性的酌减规则奉为圭臬,无视具体的交易场景以及违约金的实践功能,以司法判断代替自治安排。具体而言,无视缔约场景或者交易过程中呈现的事实因素而直接诉诸高度抽象化的酌减规则,并在同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