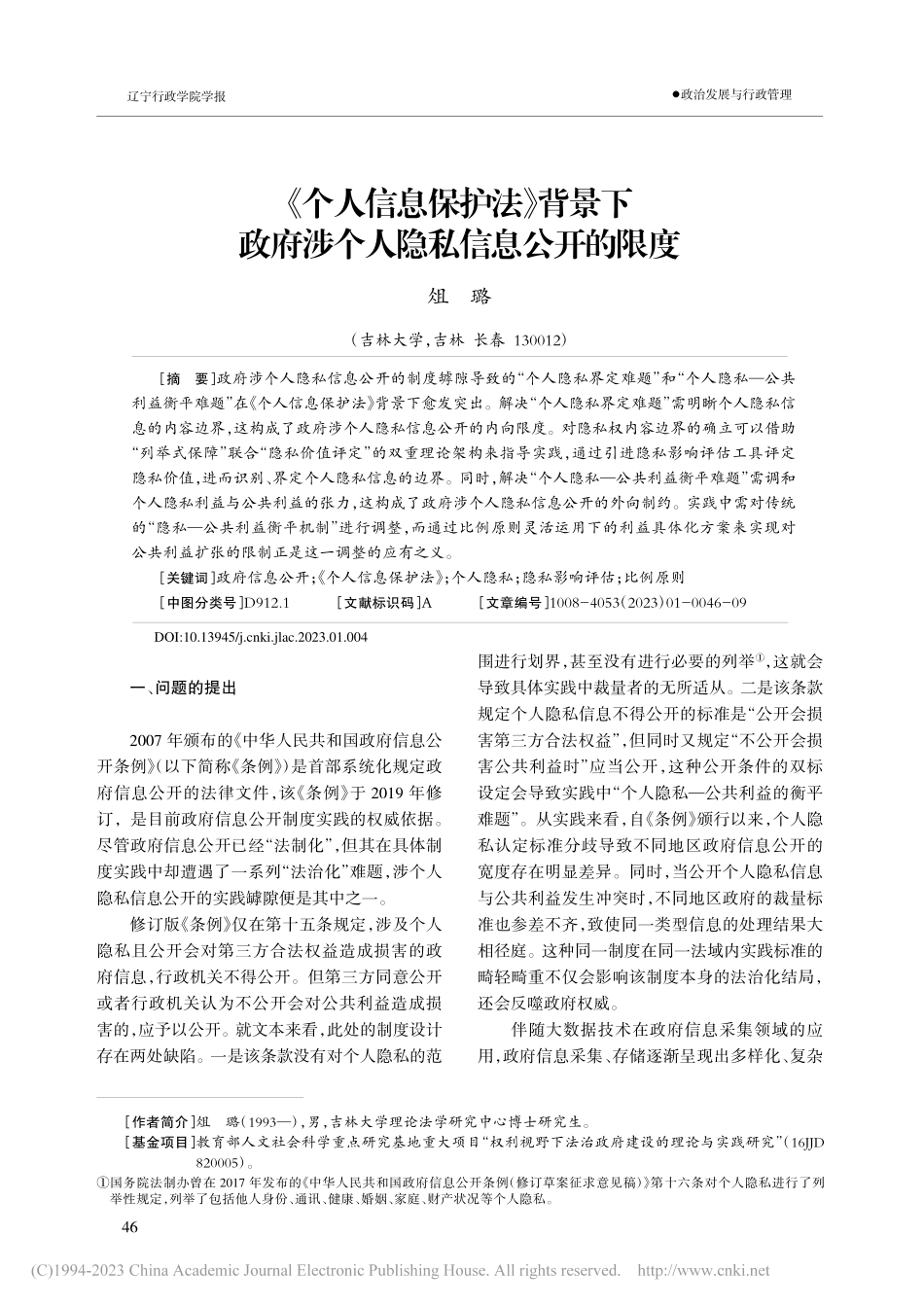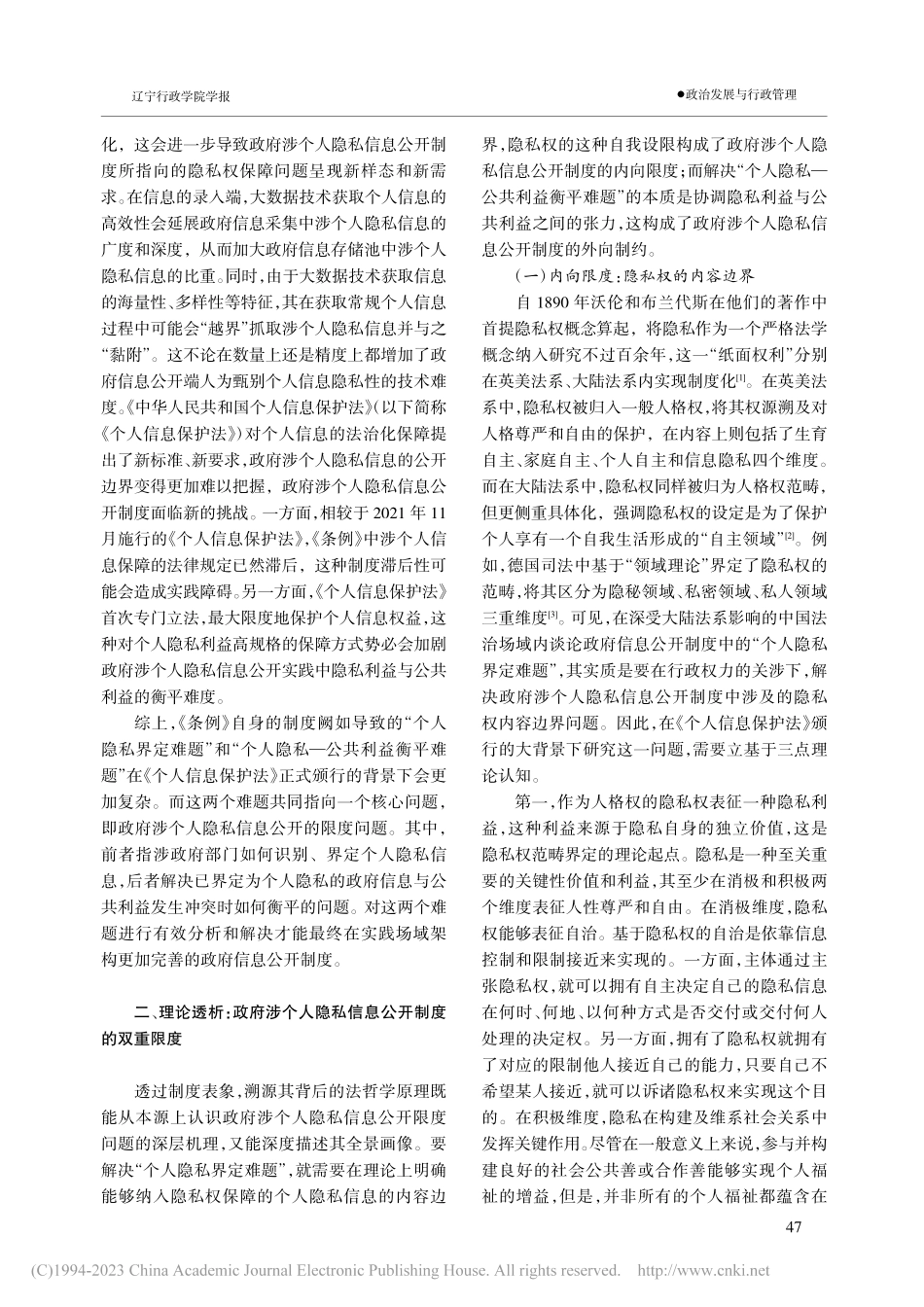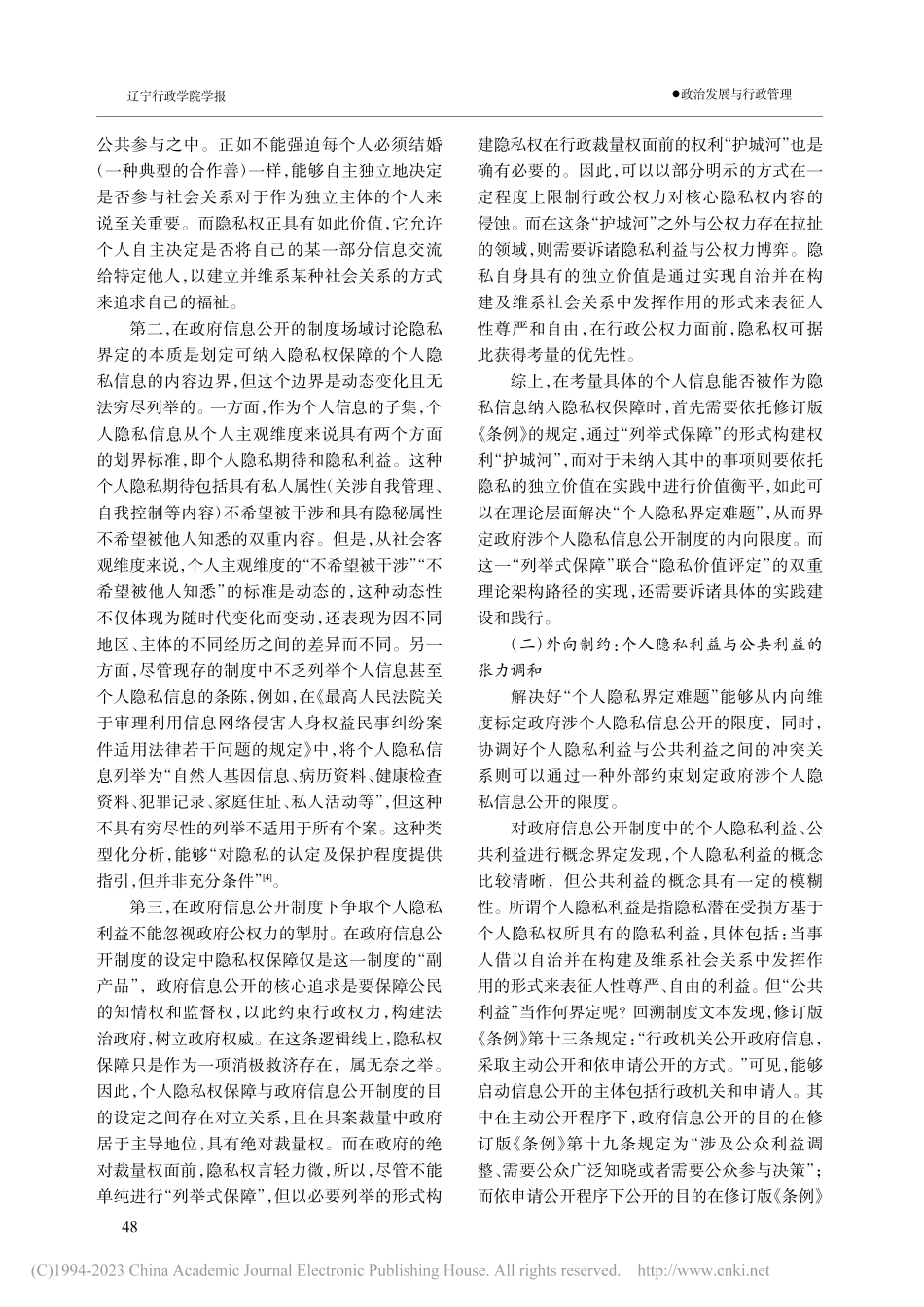辽宁行政学院学报一、问题的提出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首部系统化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文件,该《条例》于2019年修订,是目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践的权威依据。尽管政府信息公开已经“法制化”,但其在具体制度实践中却遭遇了一系列“法治化”难题,涉个人隐私信息公开的实践罅隙便是其中之一。修订版《条例》仅在第十五条规定,涉及个人隐私且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但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会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应予以公开。就文本来看,此处的制度设计存在两处缺陷。一是该条款没有对个人隐私的范围进行划界,甚至没有进行必要的列举①,这就会导致具体实践中裁量者的无所适从。二是该条款规定个人隐私信息不得公开的标准是“公开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但同时又规定“不公开会损害公共利益时”应当公开,这种公开条件的双标设定会导致实践中“个人隐私—公共利益的衡平难题”。从实践来看,自《条例》颁行以来,个人隐私认定标准分歧导致不同地区政府信息公开的宽度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当公开个人隐私信息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不同地区政府的裁量标准也参差不齐,致使同一类型信息的处理结果大相径庭。这种同一制度在同一法域内实践标准的畸轻畸重不仅会影响该制度本身的法治化结局,还会反噬政府权威。伴随大数据技术在政府信息采集领域的应用,政府信息采集、存储逐渐呈现出多样化、复杂《个人信息保护法》背景下政府涉个人隐私信息公开的限度俎璐(吉林大学,吉林长春130012)[摘要]政府涉个人隐私信息公开的制度罅隙导致的“个人隐私界定难题”和“个人隐私—公共利益衡平难题”在《个人信息保护法》背景下愈发突出。解决“个人隐私界定难题”需明晰个人隐私信息的内容边界,这构成了政府涉个人隐私信息公开的内向限度。对隐私权内容边界的确立可以借助“列举式保障”联合“隐私价值评定”的双重理论架构来指导实践,通过引进隐私影响评估工具评定隐私价值,进而识别、界定个人隐私信息的边界。同时,解决“个人隐私—公共利益衡平难题”需调和个人隐私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张力,这构成了政府涉个人隐私信息公开的外向制约。实践中需对传统的“隐私—公共利益衡平机制”进行调整,而通过比例原则灵活运用下的利益具体化方案来实现对公共利益扩张的限制正是这一调整的应有之义。[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个人信息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