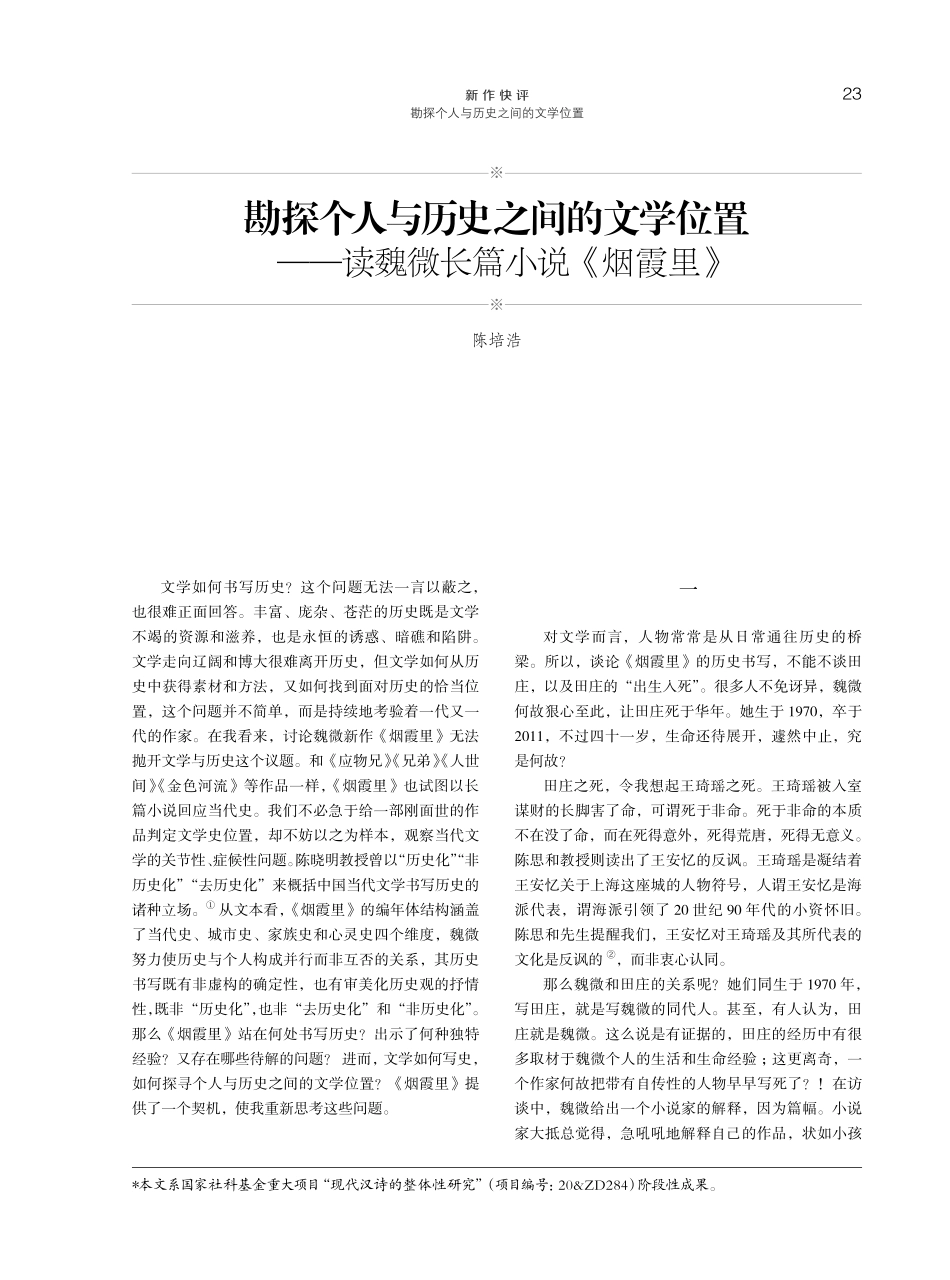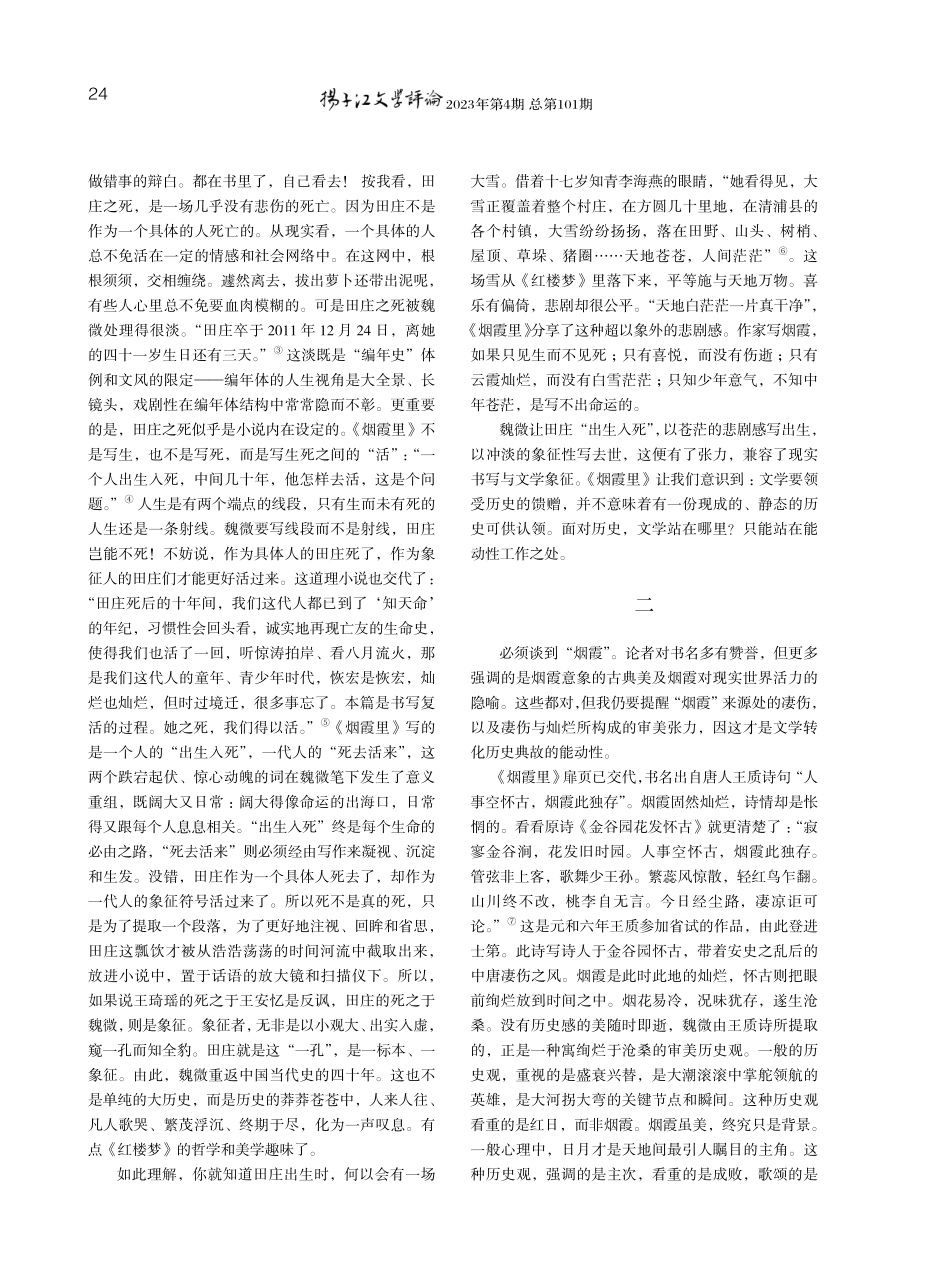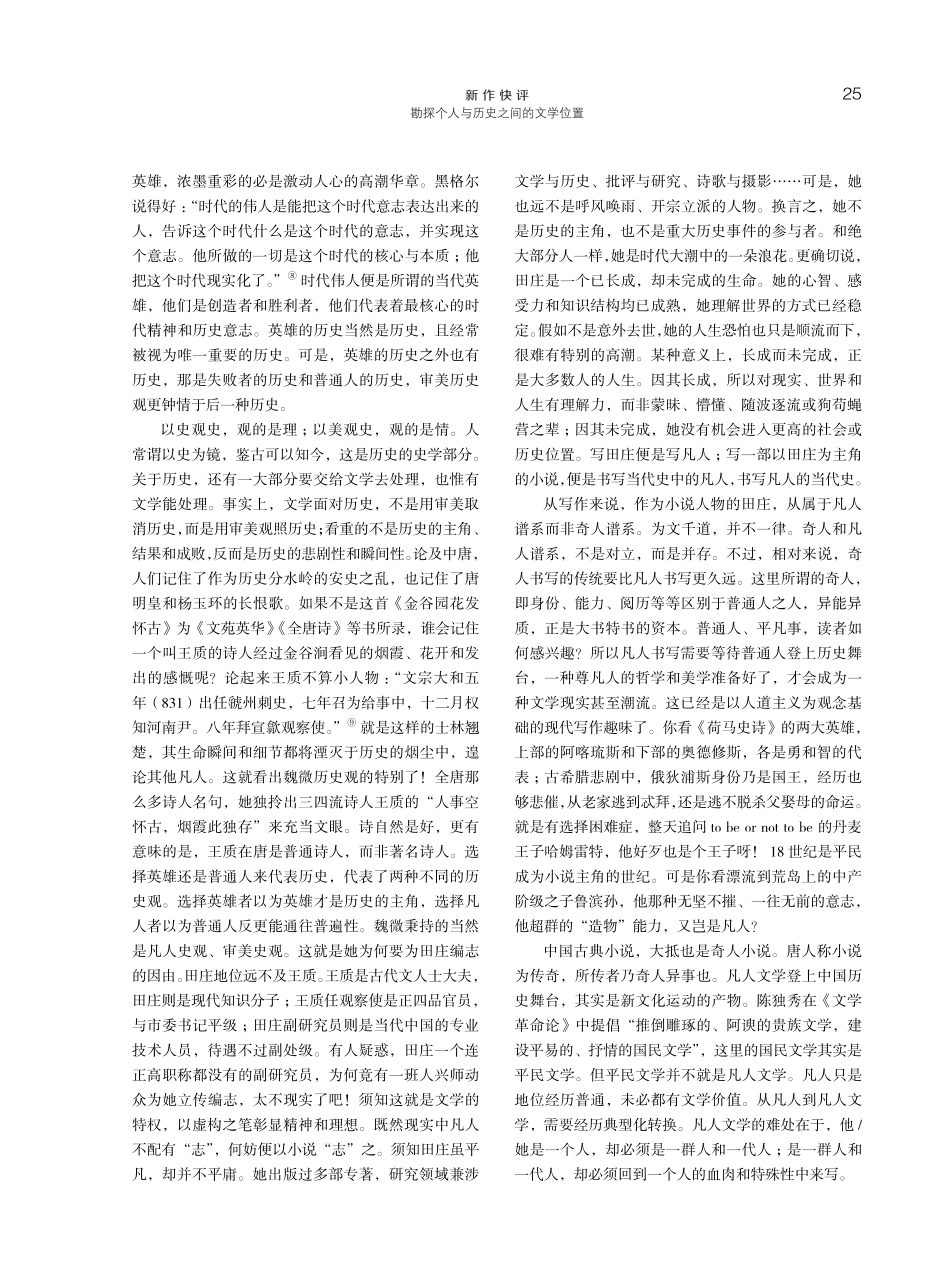23新作快评勘探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文学位置※※陈培浩文学如何书写历史?这个问题无法一言以蔽之,也很难正面回答。丰富、庞杂、苍茫的历史既是文学不竭的资源和滋养,也是永恒的诱惑、暗礁和陷阱。文学走向辽阔和博大很难离开历史,但文学如何从历史中获得素材和方法,又如何找到面对历史的恰当位置,这个问题并不简单,而是持续地考验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我看来,讨论魏微新作《烟霞里》无法抛开文学与历史这个议题。和《应物兄》《兄弟》《人世间》《金色河流》等作品一样,《烟霞里》也试图以长篇小说回应当代史。我们不必急于给一部刚面世的作品判定文学史位置,却不妨以之为样本,观察当代文学的关节性、症候性问题。陈晓明教授曾以“历史化”“非历史化”“去历史化”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书写历史的诸种立场。a从文本看,《烟霞里》的编年体结构涵盖了当代史、城市史、家族史和心灵史四个维度,魏微努力使历史与个人构成并行而非互否的关系,其历史书写既有非虚构的确定性,也有审美化历史观的抒情性,既非“历史化”,也非“去历史化”和“非历史化”。那么《烟霞里》站在何处书写历史?出示了何种独特经验?又存在哪些待解的问题?进而,文学如何写史,如何探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文学位置?《烟霞里》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重新思考这些问题。一对文学而言,人物常常是从日常通往历史的桥梁。所以,谈论《烟霞里》的历史书写,不能不谈田庄,以及田庄的“出生入死”。很多人不免讶异,魏微何故狠心至此,让田庄死于华年。她生于1970,卒于2011,不过四十一岁,生命还待展开,遽然中止,究是何故?田庄之死,令我想起王琦瑶之死。王琦瑶被入室谋财的长脚害了命,可谓死于非命。死于非命的本质不在没了命,而在死得意外,死得荒唐,死得无意义。陈思和教授则读出了王安忆的反讽。王琦瑶是凝结着王安忆关于上海这座城的人物符号,人谓王安忆是海派代表,谓海派引领了20世纪90年代的小资怀旧。陈思和先生提醒我们,王安忆对王琦瑶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是反讽的b,而非衷心认同。那么魏微和田庄的关系呢?她们同生于1970年,写田庄,就是写魏微的同代人。甚至,有人认为,田庄就是魏微。这么说是有证据的,田庄的经历中有很多取材于魏微个人的生活和生命经验;这更离奇,一个作家何故把带有自传性的人物早早写死了?!在访谈中,魏微给出一个小说家的解释,因为篇幅。小说家大抵总觉得,急吼吼地解释自己的作品,状如小孩勘探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文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