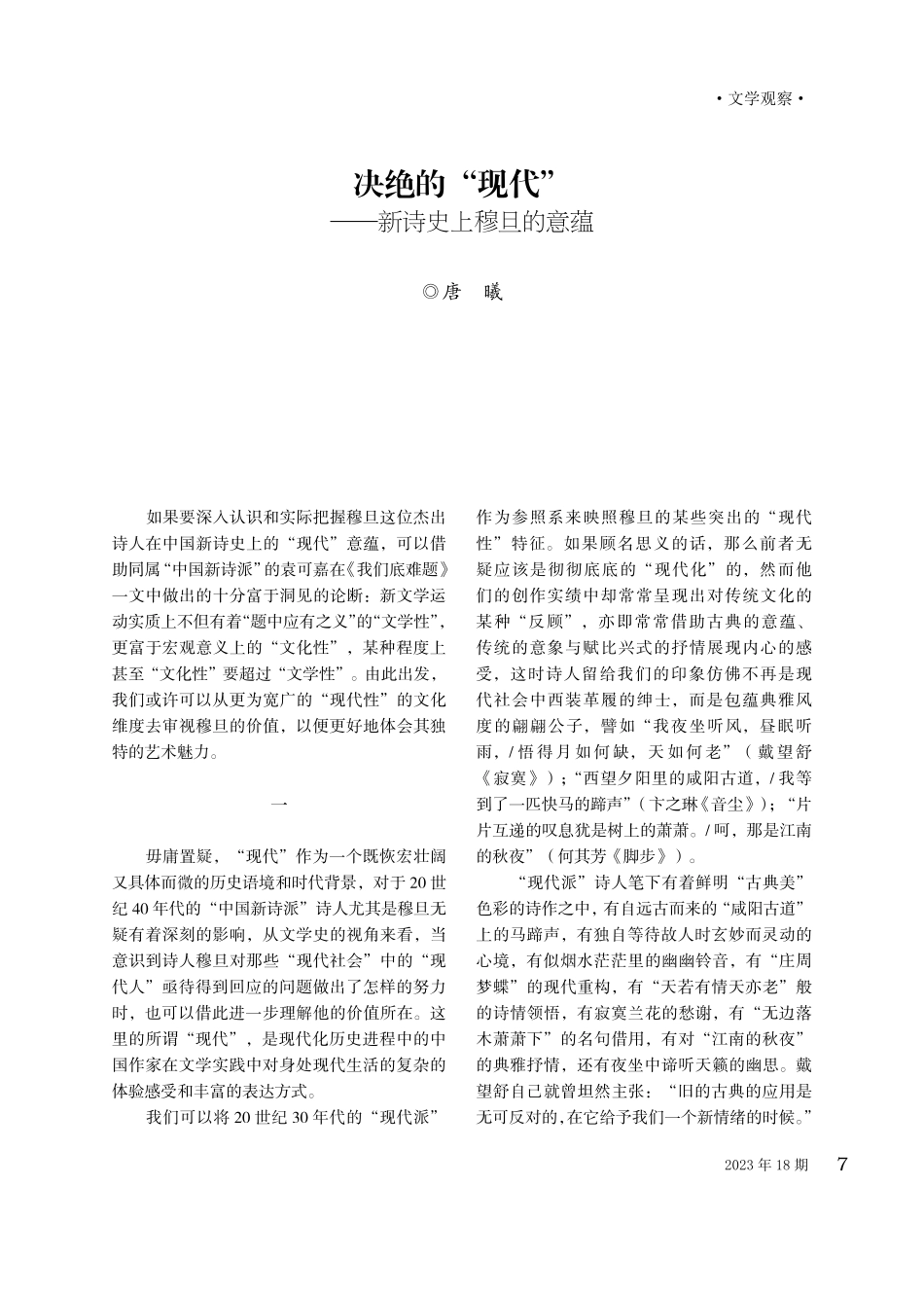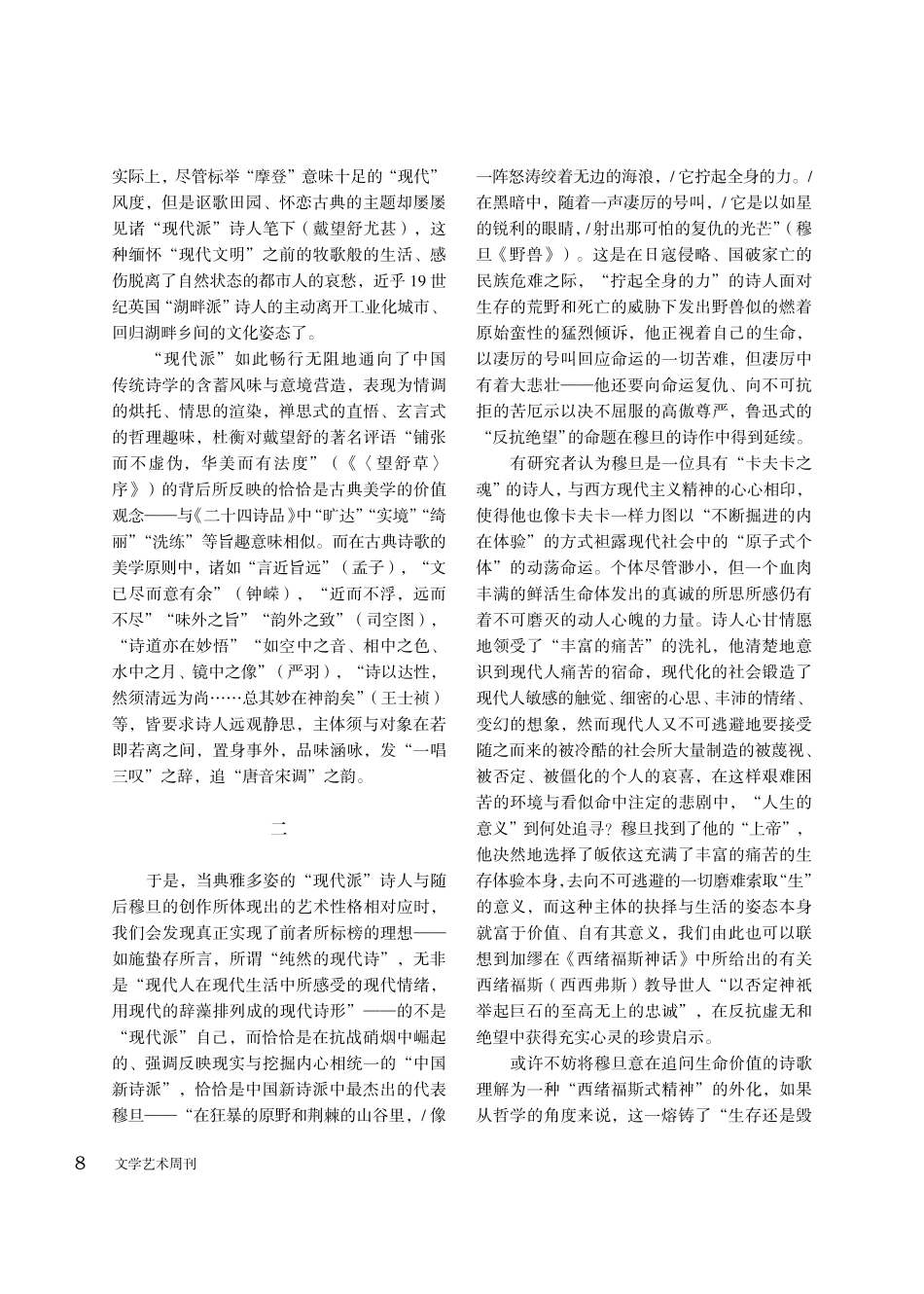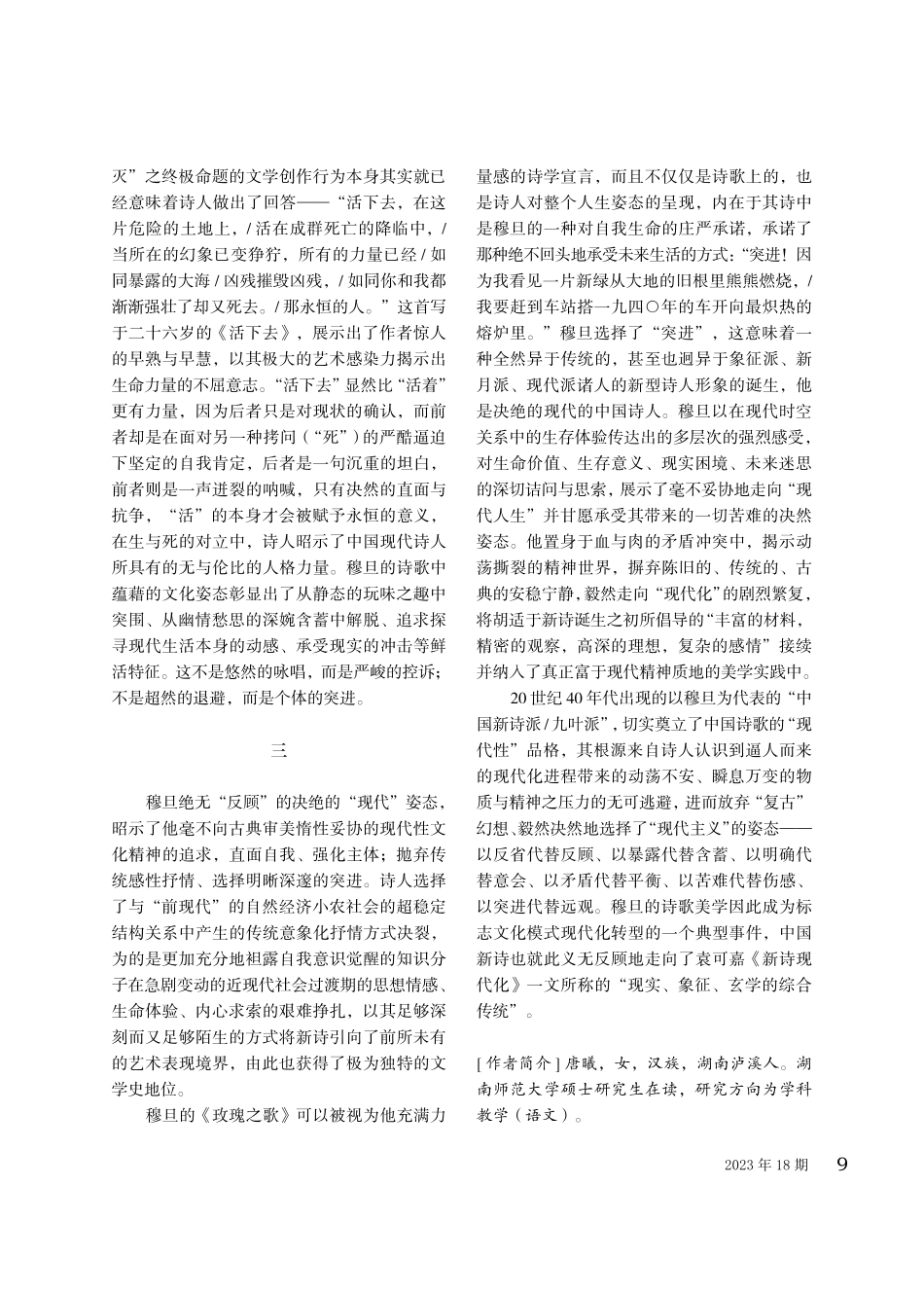2023年18期7·文学观察·如果要深入认识和实际把握穆旦这位杰出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意蕴,可以借助同属“中国新诗派”的袁可嘉在《我们底难题》一文中做出的十分富于洞见的论断:新文学运动实质上不但有着“题中应有之义”的“文学性”,更富于宏观意义上的“文化性”,某种程度上甚至“文化性”要超过“文学性”。由此出发,我们或许可以从更为宽广的“现代性”的文化维度去审视穆旦的价值,以便更好地体会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一毋庸置疑,“现代”作为一个既恢宏壮阔又具体而微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新诗派”诗人尤其是穆旦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文学史的视角来看,当意识到诗人穆旦对那些“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亟待得到回应的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努力时,也可以借此进一步理解他的价值所在。这里的所谓“现代”,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作家在文学实践中对身处现代生活的复杂的体验感受和丰富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将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作为参照系来映照穆旦的某些突出的“现代性”特征。如果顾名思义的话,那么前者无疑应该是彻彻底底的“现代化”的,然而他们的创作实绩中却常常呈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反顾”,亦即常常借助古典的意蕴、传统的意象与赋比兴式的抒情展现内心的感受,这时诗人留给我们的印象仿佛不再是现代社会中西装革履的绅士,而是包蕴典雅风度的翩翩公子,譬如“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戴望舒《寂寞》);“西望夕阳里的咸阳古道,/我等到了一匹快马的蹄声”(卞之琳《音尘》);“片片互递的叹息犹是树上的萧萧。/呵,那是江南的秋夜”(何其芳《脚步》)。“现代派”诗人笔下有着鲜明“古典美”色彩的诗作之中,有自远古而来的“咸阳古道”上的马蹄声,有独自等待故人时玄妙而灵动的心境,有似烟水茫茫里的幽幽铃音,有“庄周梦蝶”的现代重构,有“天若有情天亦老”般的诗情领悟,有寂寞兰花的愁谢,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名句借用,有对“江南的秋夜”的典雅抒情,还有夜坐中谛听天籁的幽思。戴望舒自己就曾坦然主张:“旧的古典的应用是无可反对的,在它给予我们一个新情绪的时候。”决绝的“现代”——新诗史上穆旦的意蕴◎◎唐◎曦文学艺术周刊8·文学观察·实际上,尽管标举“摩登”意味十足的“现代”风度,但是讴歌田园、怀恋古典的主题却屡屡见诸“现代派”诗人笔下(戴望舒尤甚),这种缅怀“现代文明”之前的牧歌般的生活、感伤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