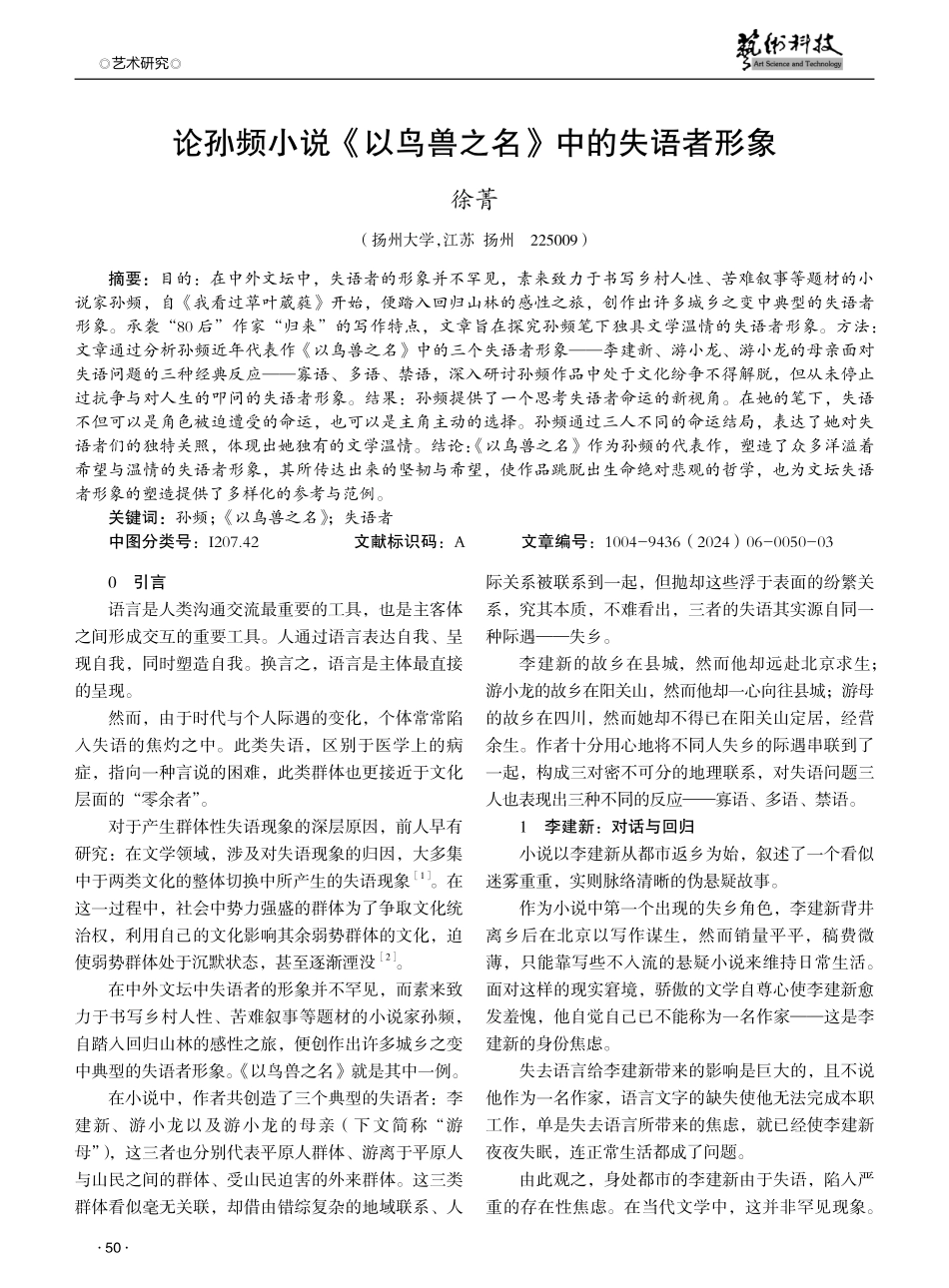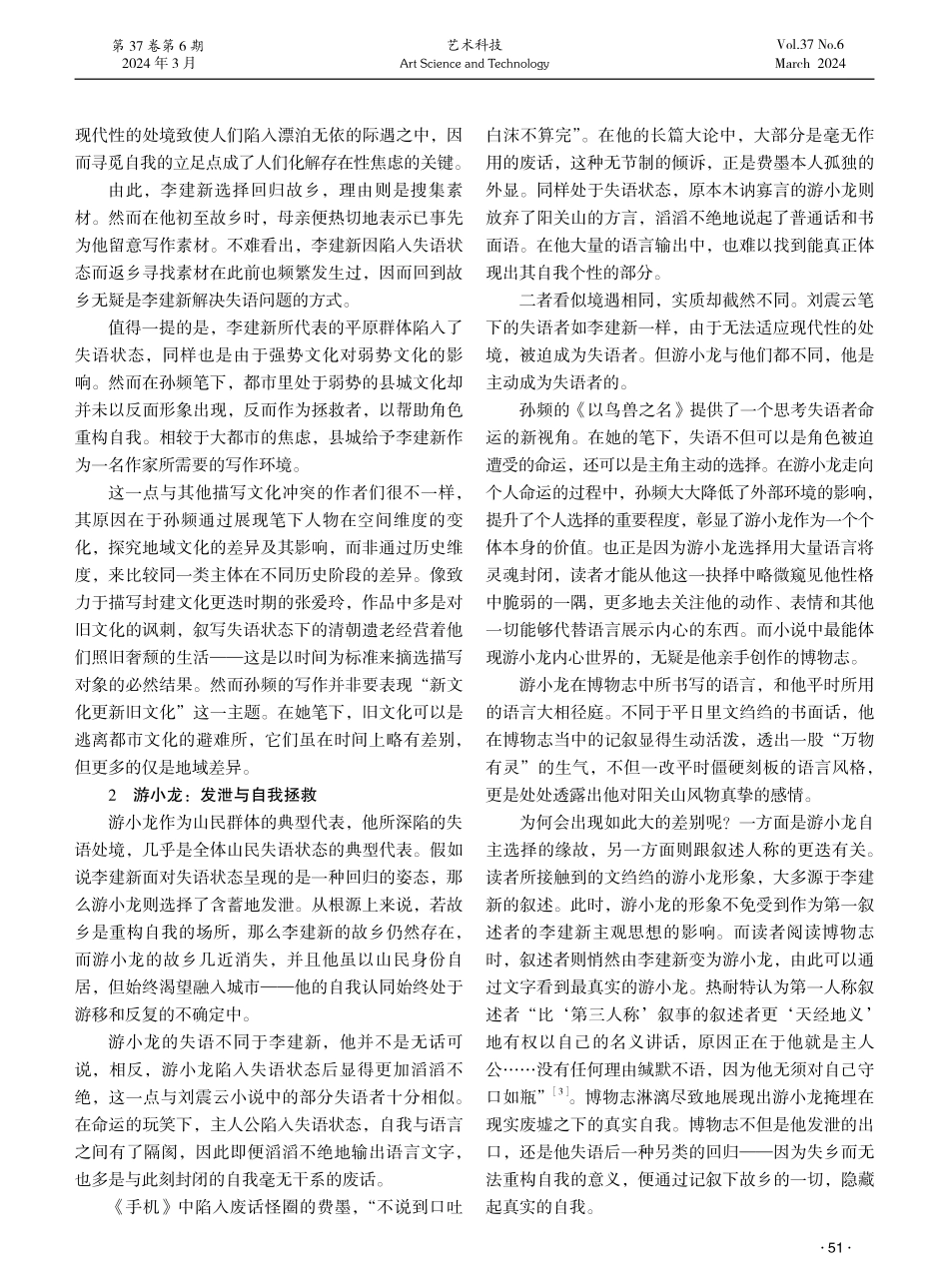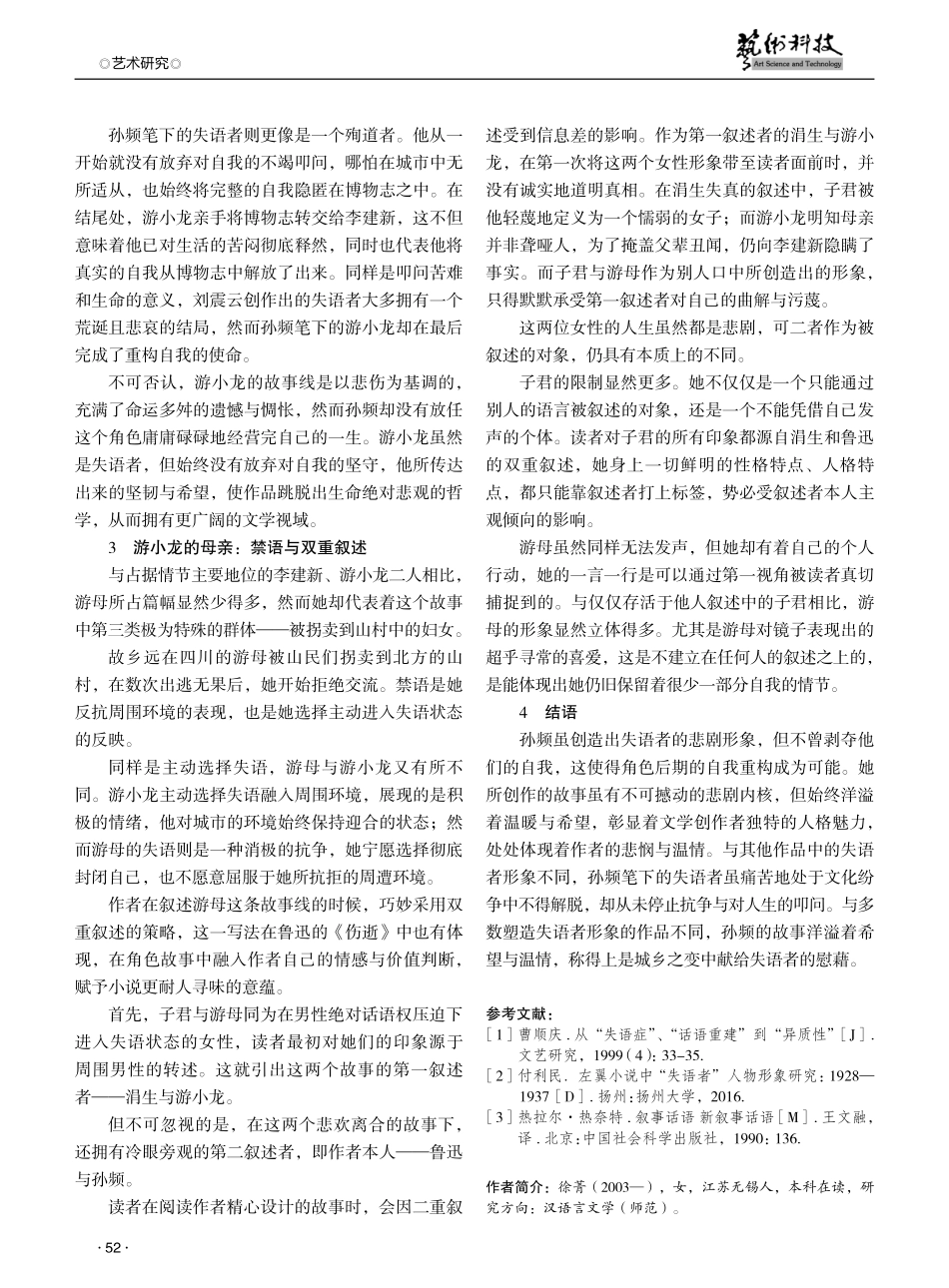·50·艺术研究0引言语言是人类沟通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也是主客体之间形成交互的重要工具。人通过语言表达自我、呈现自我,同时塑造自我。换言之,语言是主体最直接的呈现。然而,由于时代与个人际遇的变化,个体常常陷入失语的焦灼之中。此类失语,区别于医学上的病症,指向一种言说的困难,此类群体也更接近于文化层面的“零余者”。对于产生群体性失语现象的深层原因,前人早有研究:在文学领域,涉及对失语现象的归因,大多集中于两类文化的整体切换中所产生的失语现象[1]。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中势力强盛的群体为了争取文化统治权,利用自己的文化影响其余弱势群体的文化,迫使弱势群体处于沉默状态,甚至逐渐湮没[2]。在中外文坛中失语者的形象并不罕见,而素来致力于书写乡村人性、苦难叙事等题材的小说家孙频,自踏入回归山林的感性之旅,便创作出许多城乡之变中典型的失语者形象。《以鸟兽之名》就是其中一例。在小说中,作者共创造了三个典型的失语者:李建新、游小龙以及游小龙的母亲(下文简称“游母”),这三者也分别代表平原人群体、游离于平原人与山民之间的群体、受山民迫害的外来群体。这三类群体看似毫无关联,却借由错综复杂的地域联系、人际关系被联系到一起,但抛却这些浮于表面的纷繁关系,究其本质,不难看出,三者的失语其实源自同一种际遇——失乡。李建新的故乡在县城,然而他却远赴北京求生;游小龙的故乡在阳关山,然而他却一心向往县城;游母的故乡在四川,然而她却不得已在阳关山定居,经营余生。作者十分用心地将不同人失乡的际遇串联到了一起,构成三对密不可分的地理联系,对失语问题三人也表现出三种不同的反应——寡语、多语、禁语。1李建新:对话与回归小说以李建新从都市返乡为始,叙述了一个看似迷雾重重,实则脉络清晰的伪悬疑故事。作为小说中第一个出现的失乡角色,李建新背井离乡后在北京以写作谋生,然而销量平平,稿费微薄,只能靠写些不入流的悬疑小说来维持日常生活。面对这样的现实窘境,骄傲的文学自尊心使李建新愈发羞愧,他自觉自己已不能称为一名作家——这是李建新的身份焦虑。失去语言给李建新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且不说他作为一名作家,语言文字的缺失使他无法完成本职工作,单是失去语言所带来的焦虑,就已经使李建新夜夜失眠,连正常生活都成了问题。由此观之,身处都市的李建新由于失语,陷入严重的存在性焦虑。在当代文学中,这并非罕见现象。论孙频小说《以鸟兽之名》中的失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