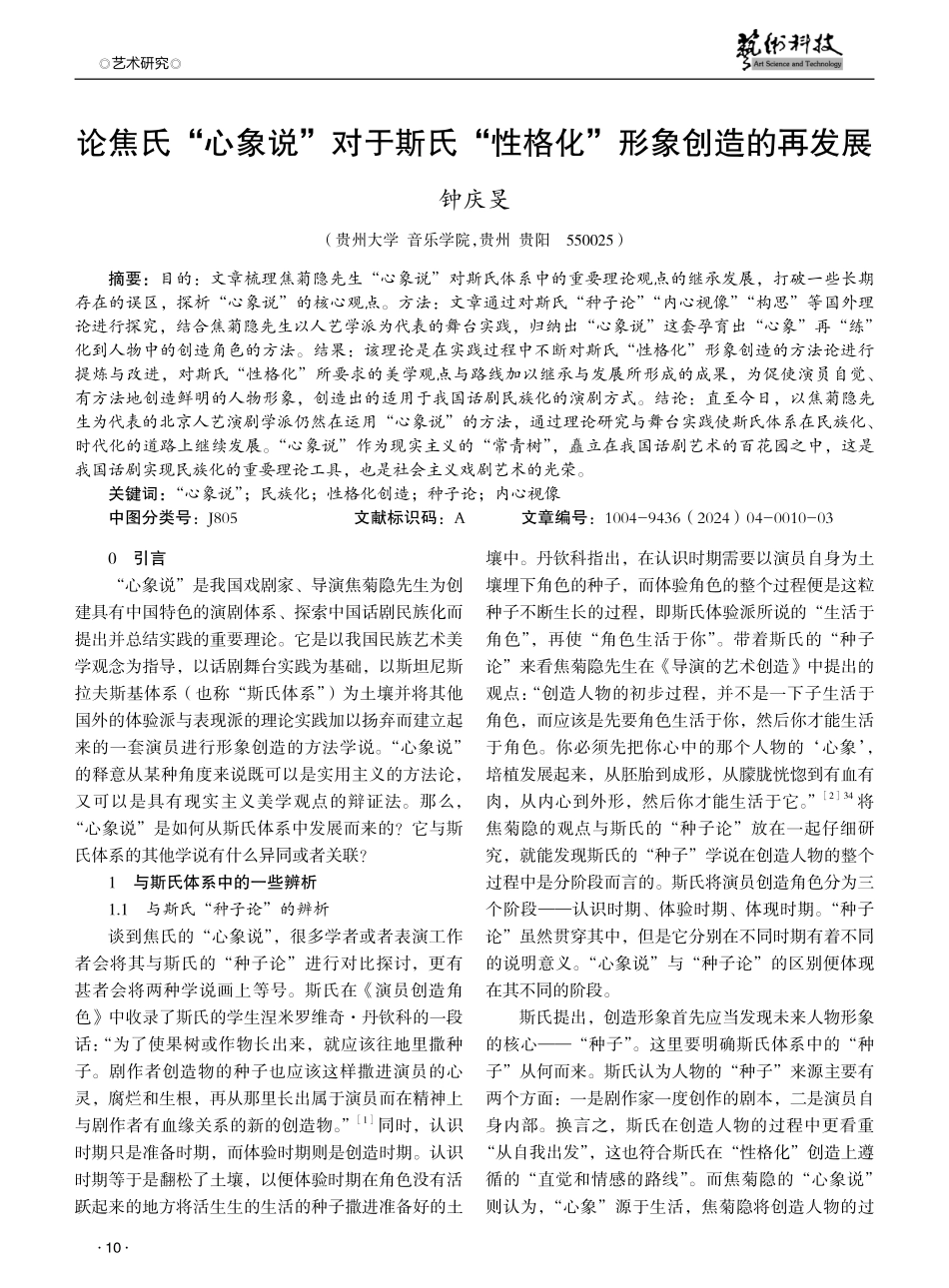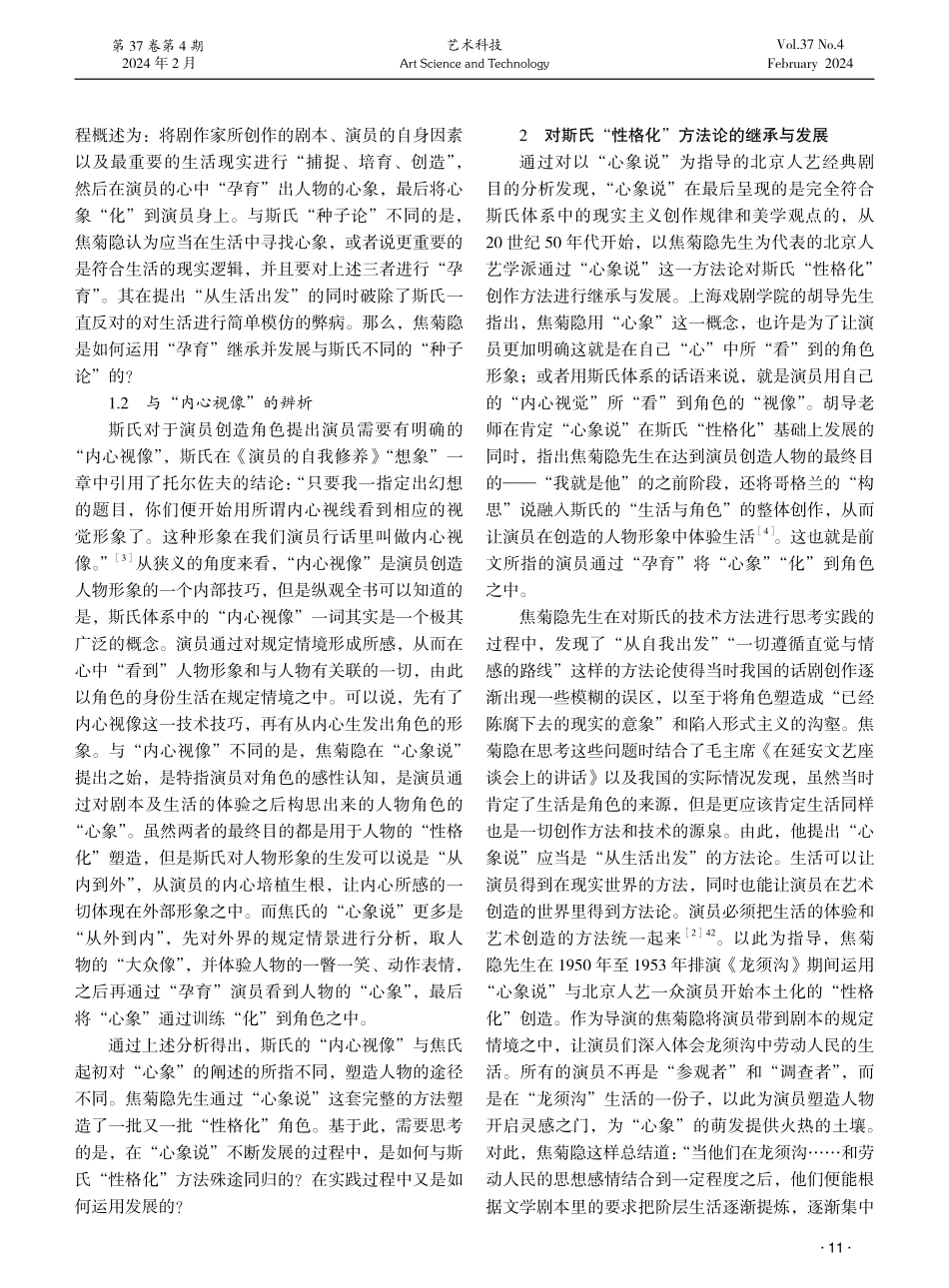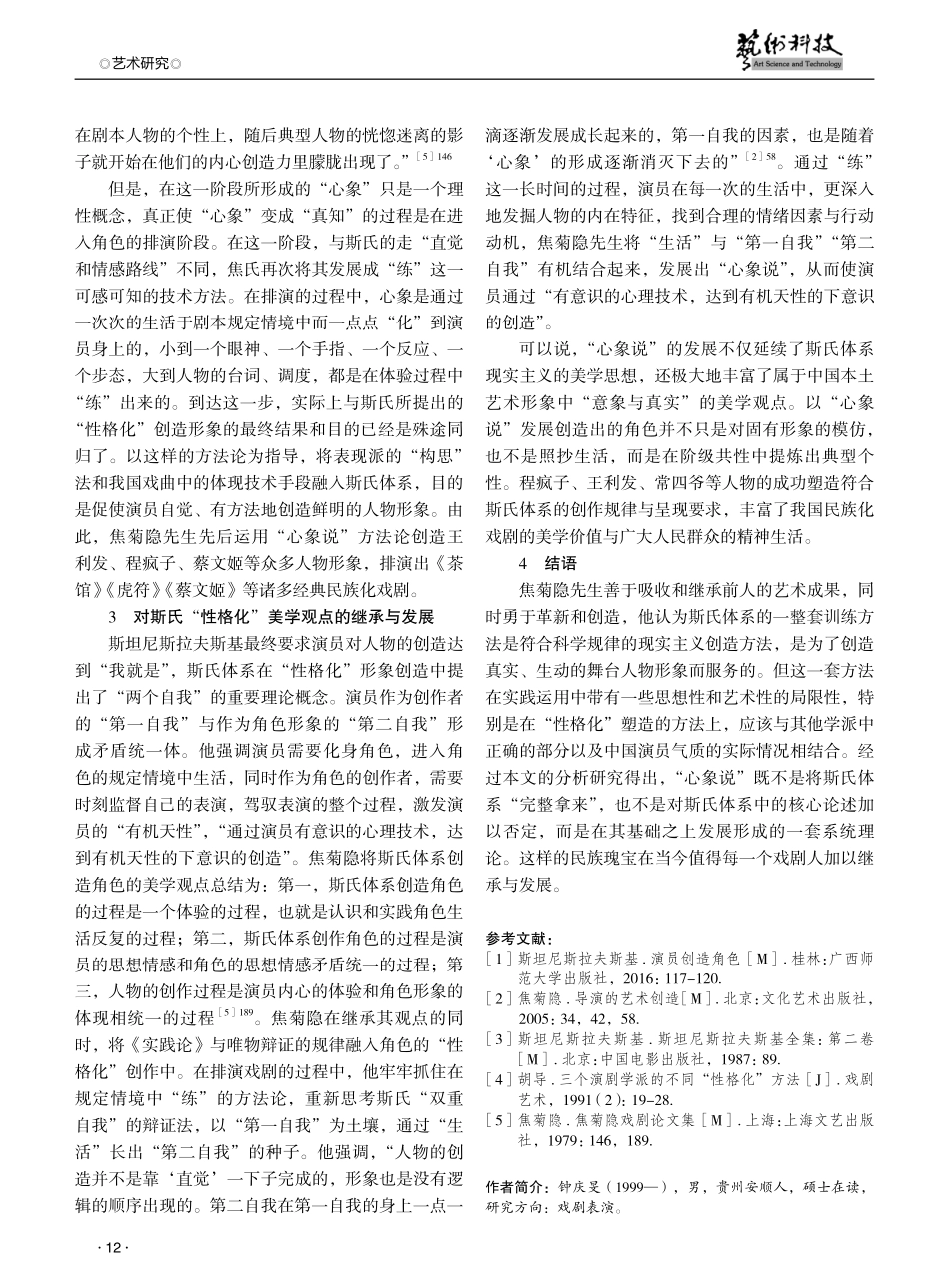·10·艺术研究0…引言“心象说”是我国戏剧家、导演焦菊隐先生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演剧体系、探索中国话剧民族化而提出并总结实践的重要理论。它是以我国民族艺术美学观念为指导,以话剧舞台实践为基础,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也称“斯氏体系”)为土壤并将其他国外的体验派与表现派的理论实践加以扬弃而建立起来的一套演员进行形象创造的方法学说。“心象说”的释意从某种角度来说既可以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又可以是具有现实主义美学观点的辩证法。那么,“心象说”是如何从斯氏体系中发展而来的?它与斯氏体系的其他学说有什么异同或者关联?1…与斯氏体系中的一些辨析1.1…与斯氏“种子论”的辨析谈到焦氏的“心象说”,很多学者或者表演工作者会将其与斯氏的“种子论”进行对比探讨,更有甚者会将两种学说画上等号。斯氏在《演员创造角色》中收录了斯氏的学生涅米罗维奇·丹钦科的一段话:“为了使果树或作物长出来,就应该往地里撒种子。剧作者创造物的种子也应该这样撒进演员的心灵,腐烂和生根,再从那里长出属于演员而在精神上与剧作者有血缘关系的新的创造物。”[1]同时,认识时期只是准备时期,而体验时期则是创造时期。认识时期等于是翻松了土壤,以便体验时期在角色没有活跃起来的地方将活生生的生活的种子撒进准备好的土壤中。丹钦科指出,在认识时期需要以演员自身为土壤埋下角色的种子,而体验角色的整个过程便是这粒种子不断生长的过程,即斯氏体验派所说的“生活于角色”,再使“角色生活于你”。带着斯氏的“种子论”来看焦菊隐先生在《导演的艺术创造》中提出的观点:“创造人物的初步过程,并不是一下子生活于角色,而应该是先要角色生活于你,然后你才能生活于角色。你必须先把你心中的那个人物的‘心象’,培植发展起来,从胚胎到成形,从朦胧恍惚到有血有肉,从内心到外形,然后你才能生活于它。”[2]34将焦菊隐的观点与斯氏的“种子论”放在一起仔细研究,就能发现斯氏的“种子”学说在创造人物的整个过程中是分阶段而言的。斯氏将演员创造角色分为三个阶段——认识时期、体验时期、体现时期。“种子论”虽然贯穿其中,但是它分别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说明意义。“心象说”与“种子论”的区别便体现在其不同的阶段。斯氏提出,创造形象首先应当发现未来人物形象的核心——“种子”。这里要明确斯氏体系中的“种子”从何而来。斯氏认为人物的“种子”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剧作家一度创作的剧本,二是演员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