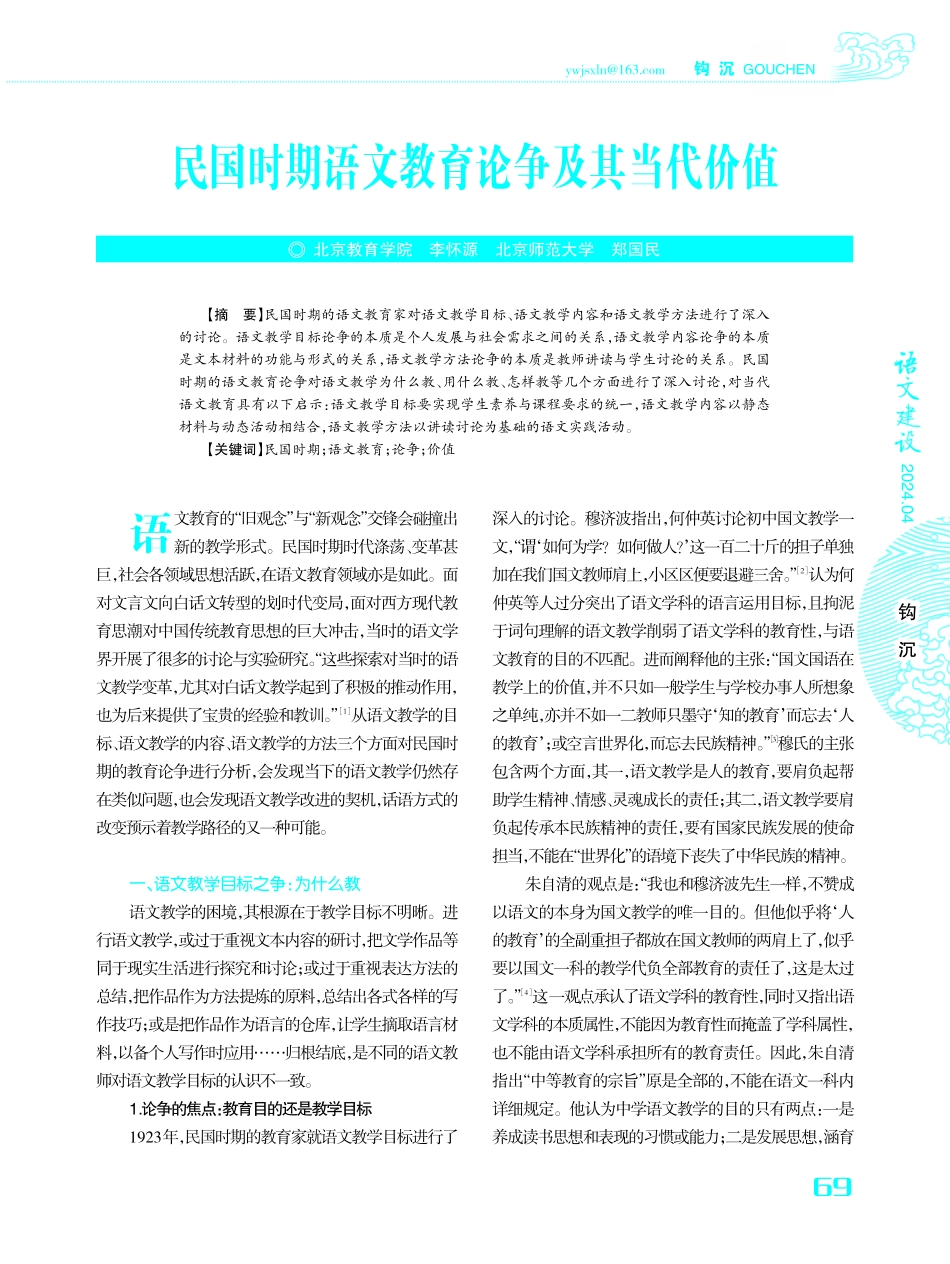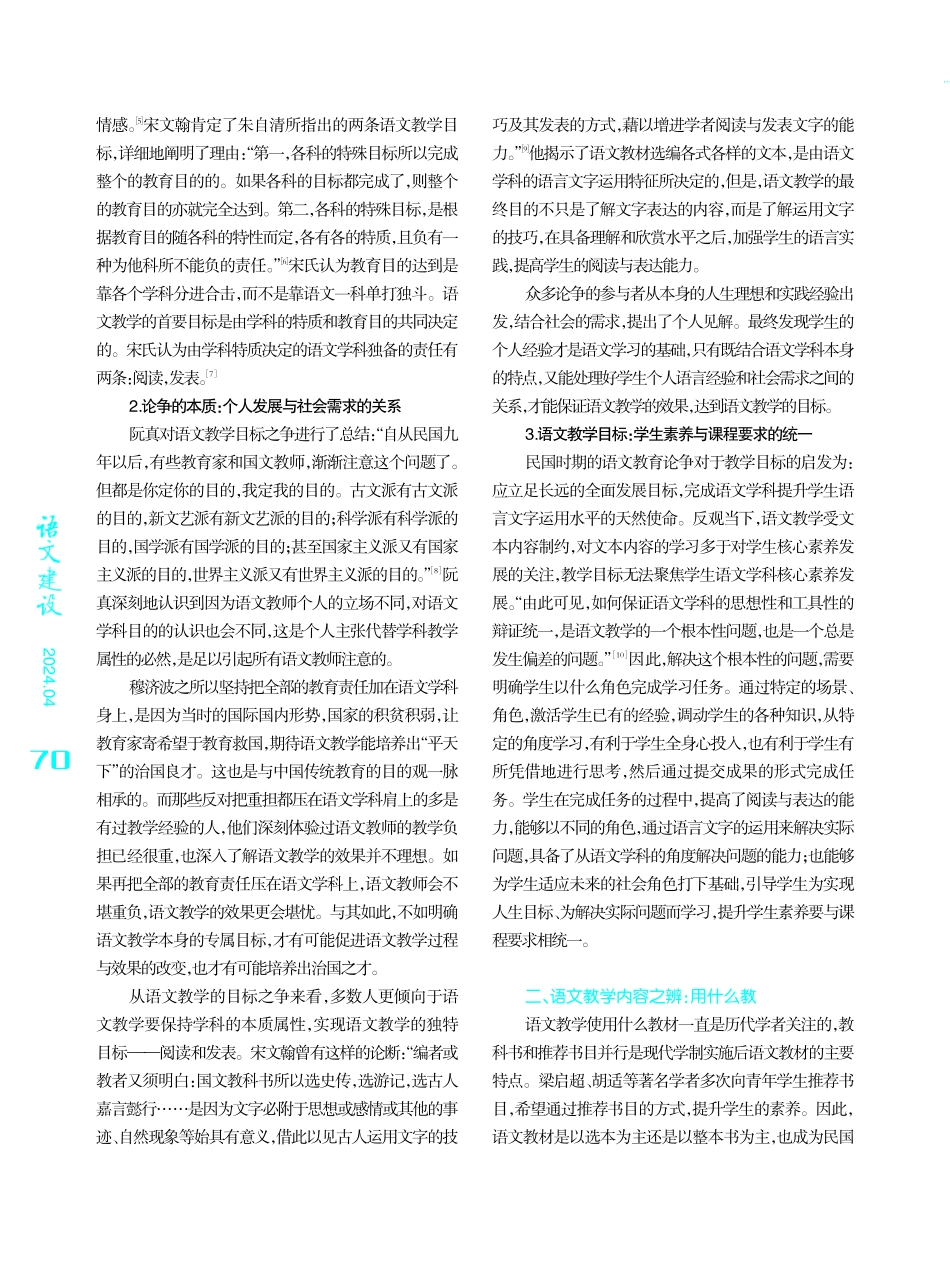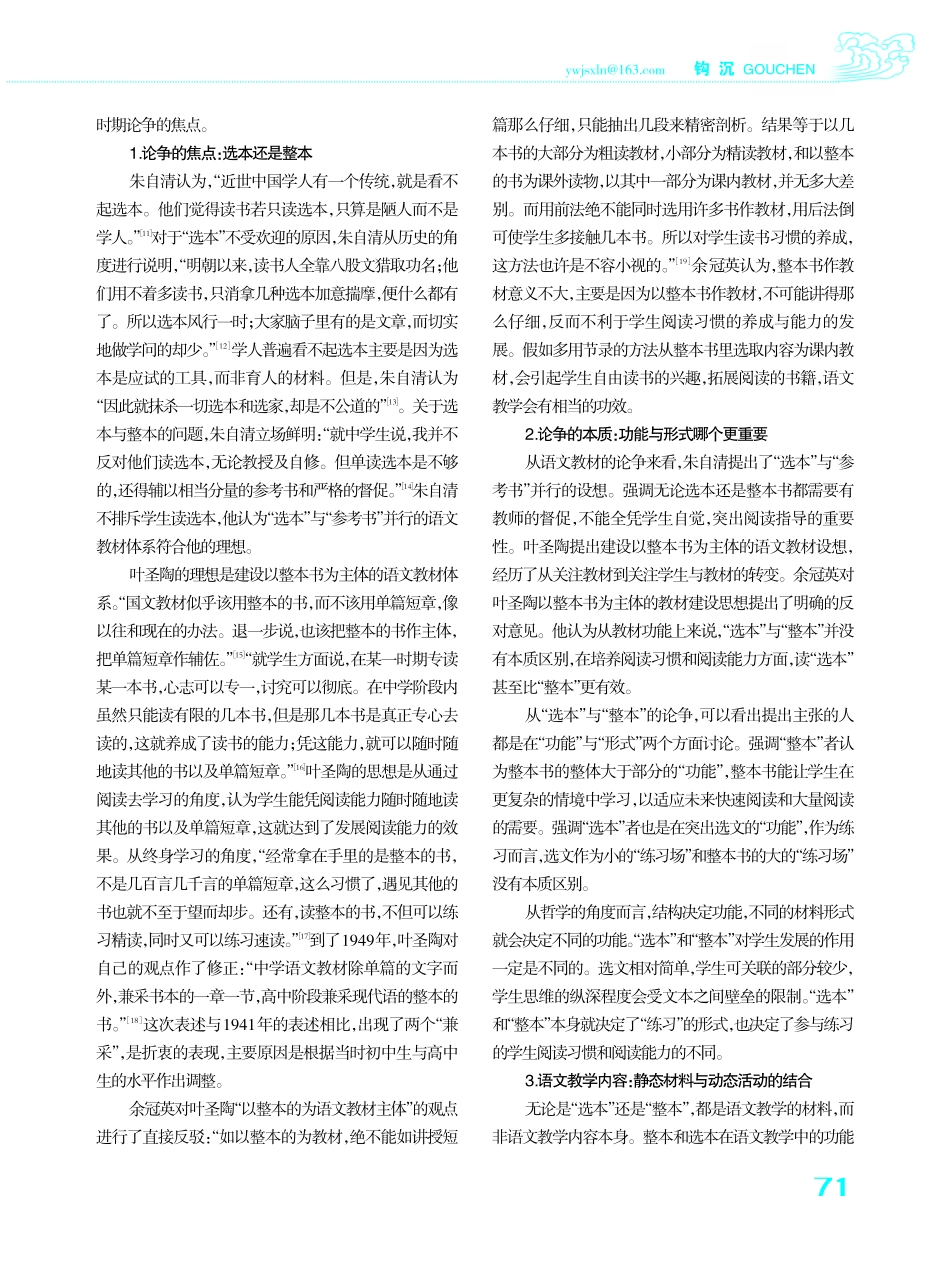ywjsxln@163.com钩沉GOUCHEN语文教育的“旧观念”与“新观念”交锋会碰撞出新的教学形式。民国时期时代涤荡、变革甚巨,社会各领域思想活跃,在语文教育领域亦是如此。面对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的划时代变局,面对西方现代教育思潮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巨大冲击,当时的语文学界开展了很多的讨论与实验研究。“这些探索对当时的语文教学变革,尤其对白话文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后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1]从语文教学的目标、语文教学的内容、语文教学的方法三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的教育论争进行分析,会发现当下的语文教学仍然存在类似问题,也会发现语文教学改进的契机,话语方式的改变预示着教学路径的又一种可能。一、语文教学目标之争:为什么教语文教学的困境,其根源在于教学目标不明晰。进行语文教学,或过于重视文本内容的研讨,把文学作品等同于现实生活进行探究和讨论;或过于重视表达方法的总结,把作品作为方法提炼的原料,总结出各式各样的写作技巧;或是把作品作为语言的仓库,让学生摘取语言材料,以备个人写作时应用……归根结底,是不同的语文教师对语文教学目标的认识不一致。1.论争的焦点:教育目的还是教学目标1923年,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就语文教学目标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穆济波指出,何仲英讨论初中国文教学一文,“谓‘如何为学?如何做人?’这一百二十斤的担子单独加在我们国文教师肩上,小区区便要退避三舍。”[2]认为何仲英等人过分突出了语文学科的语言运用目标,且拘泥于词句理解的语文教学削弱了语文学科的教育性,与语文教育的目的不匹配。进而阐释他的主张:“国文国语在教学上的价值,并不只如一般学生与学校办事人所想象之单纯,亦并不如一二教师只墨守‘知的教育’而忘去‘人的教育’;或空言世界化,而忘去民族精神。”[3]穆氏的主张包含两个方面,其一,语文教学是人的教育,要肩负起帮助学生精神、情感、灵魂成长的责任;其二,语文教学要肩负起传承本民族精神的责任,要有国家民族发展的使命担当,不能在“世界化”的语境下丧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朱自清的观点是:“我也和穆济波先生一样,不赞成以语文的本身为国文教学的唯一目的。但他似乎将‘人的教育’的全副重担子都放在国文教师的两肩上了,似乎要以国文一科的教学代负全部教育的责任了,这是太过了。”[4]这一观点承认了语文学科的教育性,同时又指出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不能因为教育性而掩盖了学科属性,也不能由语文学科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