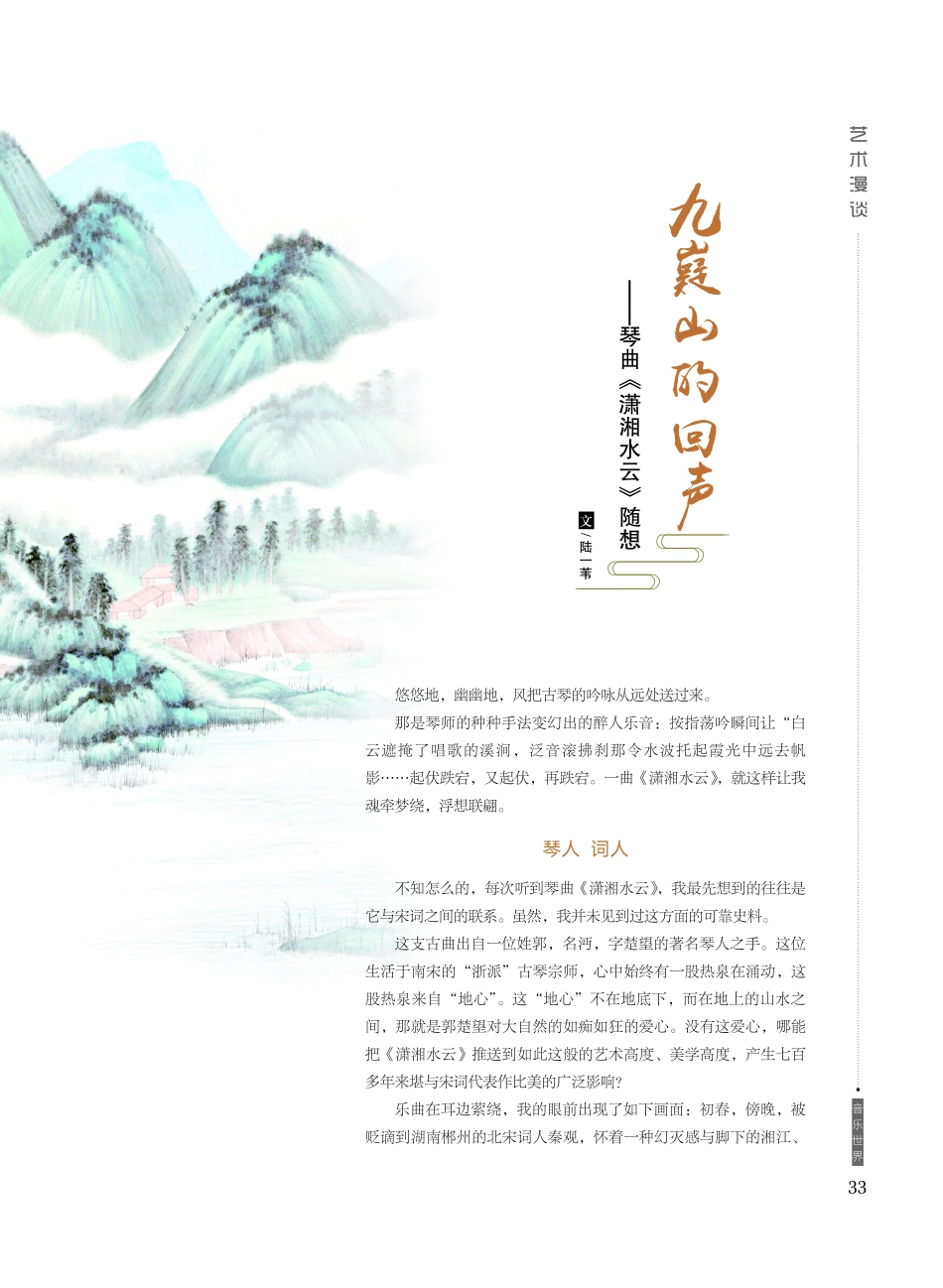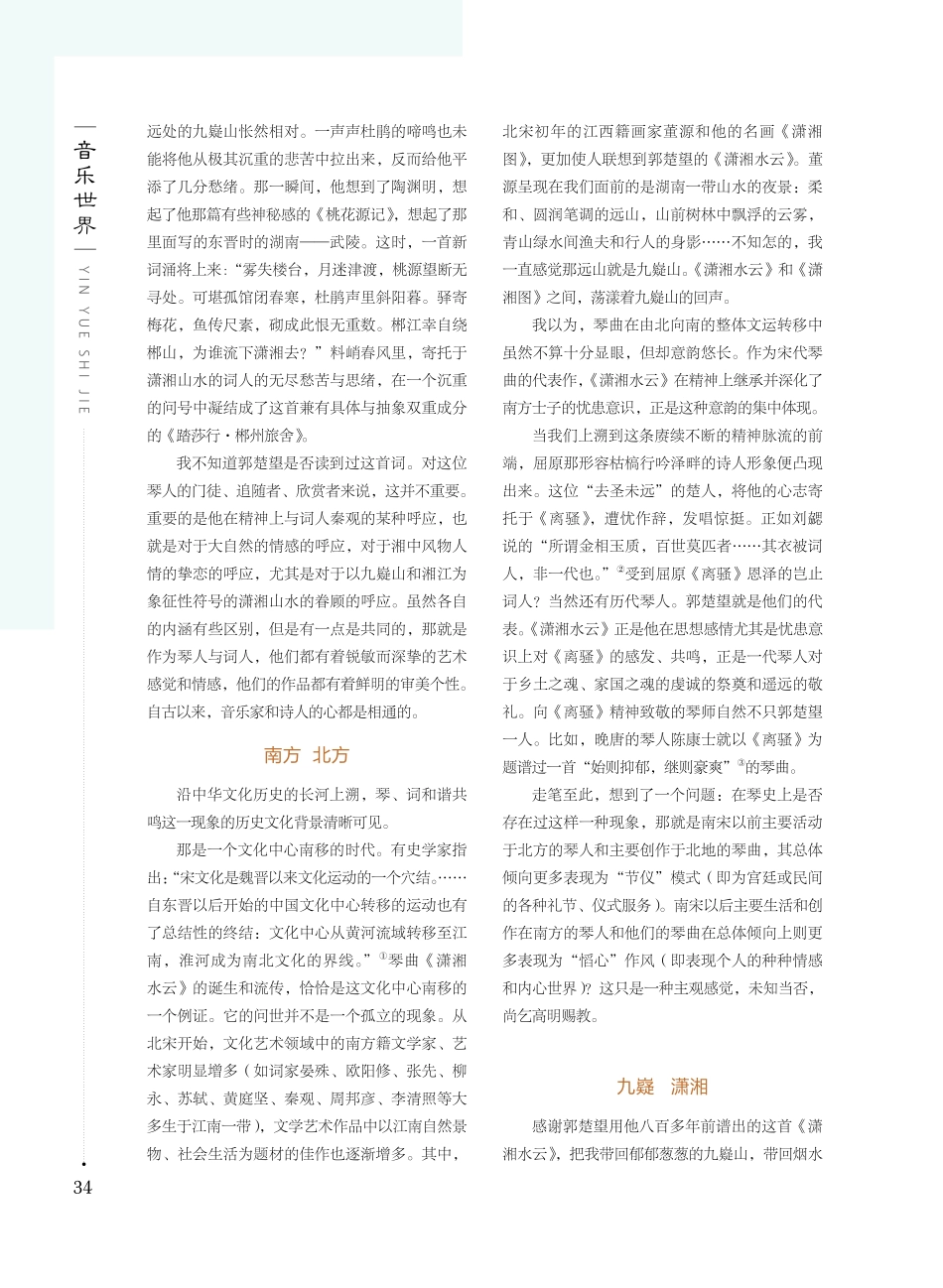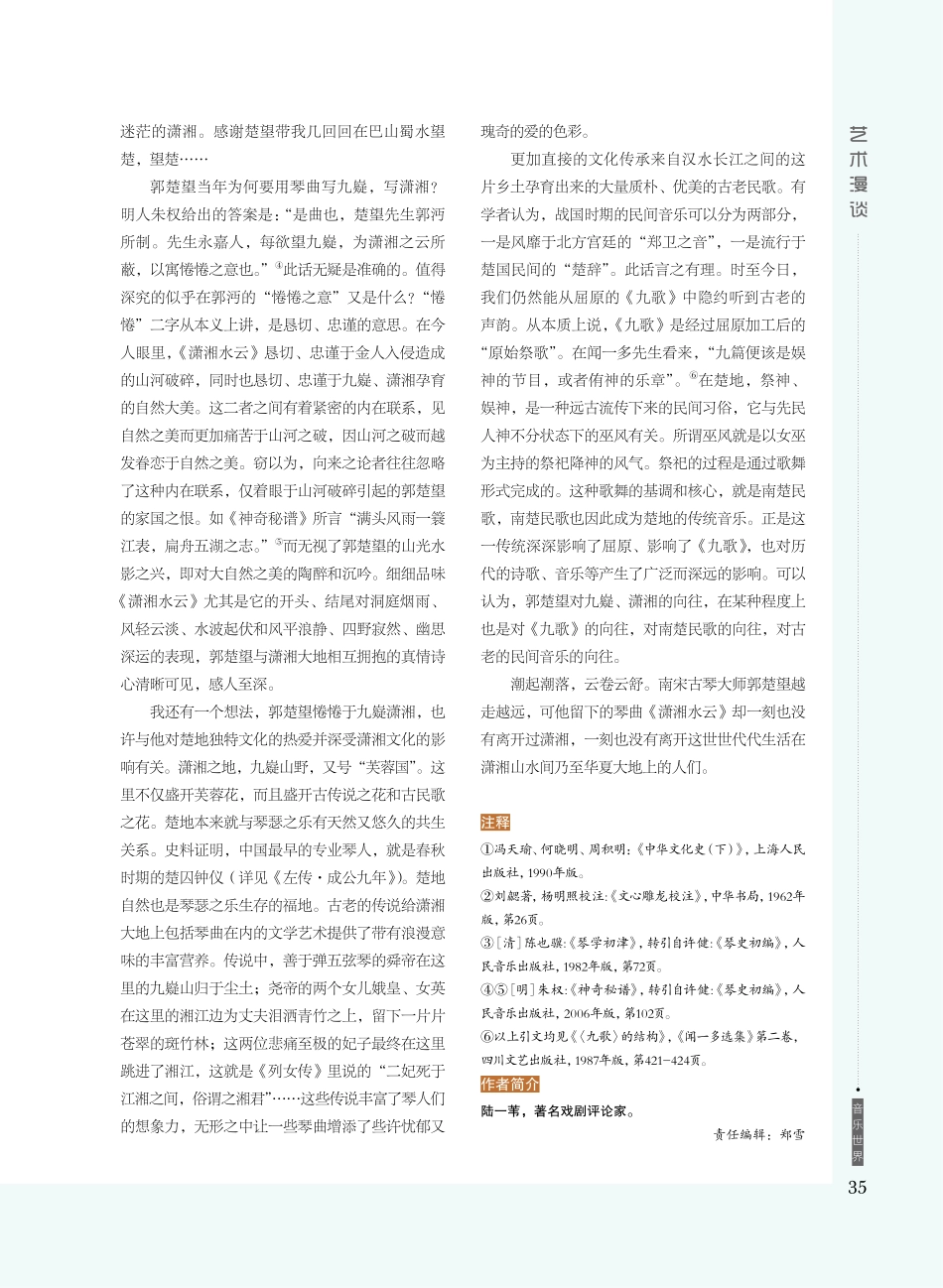悠悠地,幽幽地,风把古琴的吟咏从远处送过来。那是琴师的种种手法变幻出的醉人乐音:按指荡吟瞬间让“白云遮掩了唱歌的溪涧,泛音滚拂刹那令水波托起霞光中远去帆影……起伏跌宕,又起伏,再跌宕。一曲《潇湘水云》,就这样让我魂牵梦绕,浮想联翩。琴人词人不知怎么的,每次听到琴曲《潇湘水云》,我最先想到的往往是它与宋词之间的联系。虽然,我并未见到过这方面的可靠史料。这支古曲出自一位姓郭,名沔,字楚望的著名琴人之手。这位生活于南宋的“浙派”古琴宗师,心中始终有一股热泉在涌动,这股热泉来自“地心”。这“地心”不在地底下,而在地上的山水之间,那就是郭楚望对大自然的如痴如狂的爱心。没有这爱心,哪能把《潇湘水云》推送到如此这般的艺术高度、美学高度,产生七百多年来堪与宋词代表作比美的广泛影响?乐曲在耳边萦绕,我的眼前出现了如下画面:初春,傍晚,被贬谪到湖南郴州的北宋词人秦观,怀着一种幻灭感与脚下的湘江、九嶷山的回声文/陆一苇——琴曲《潇湘水云》随想艺术漫谈33音乐世界远处的九嶷山怅然相对。一声声杜鹃的啼鸣也未能将他从极其沉重的悲苦中拉出来,反而给他平添了几分愁绪。那一瞬间,他想到了陶渊明,想起了他那篇有些神秘感的《桃花源记》,想起了那里面写的东晋时的湖南——武陵。这时,一首新词涌将上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料峭春风里,寄托于潇湘山水的词人的无尽愁苦与思绪,在一个沉重的问号中凝结成了这首兼有具体与抽象双重成分的《踏莎行·郴州旅舍》。我不知道郭楚望是否读到过这首词。对这位琴人的门徒、追随者、欣赏者来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精神上与词人秦观的某种呼应,也就是对于大自然的情感的呼应,对于湘中风物人情的挚恋的呼应,尤其是对于以九嶷山和湘江为象征性符号的潇湘山水的眷顾的呼应。虽然各自的内涵有些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作为琴人与词人,他们都有着锐敏而深挚的艺术感觉和情感,他们的作品都有着鲜明的审美个性。自古以来,音乐家和诗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南方北方沿中华文化历史的长河上溯,琴、词和谐共鸣这一现象的历史文化背景清晰可见。那是一个文化中心南移的时代。有史学家指出:“宋文化是魏晋以来文化运动的一个穴结。……自东晋以后开始的中国文化中心转移的运动也有了总结性的终结:文化中心从黄河流域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