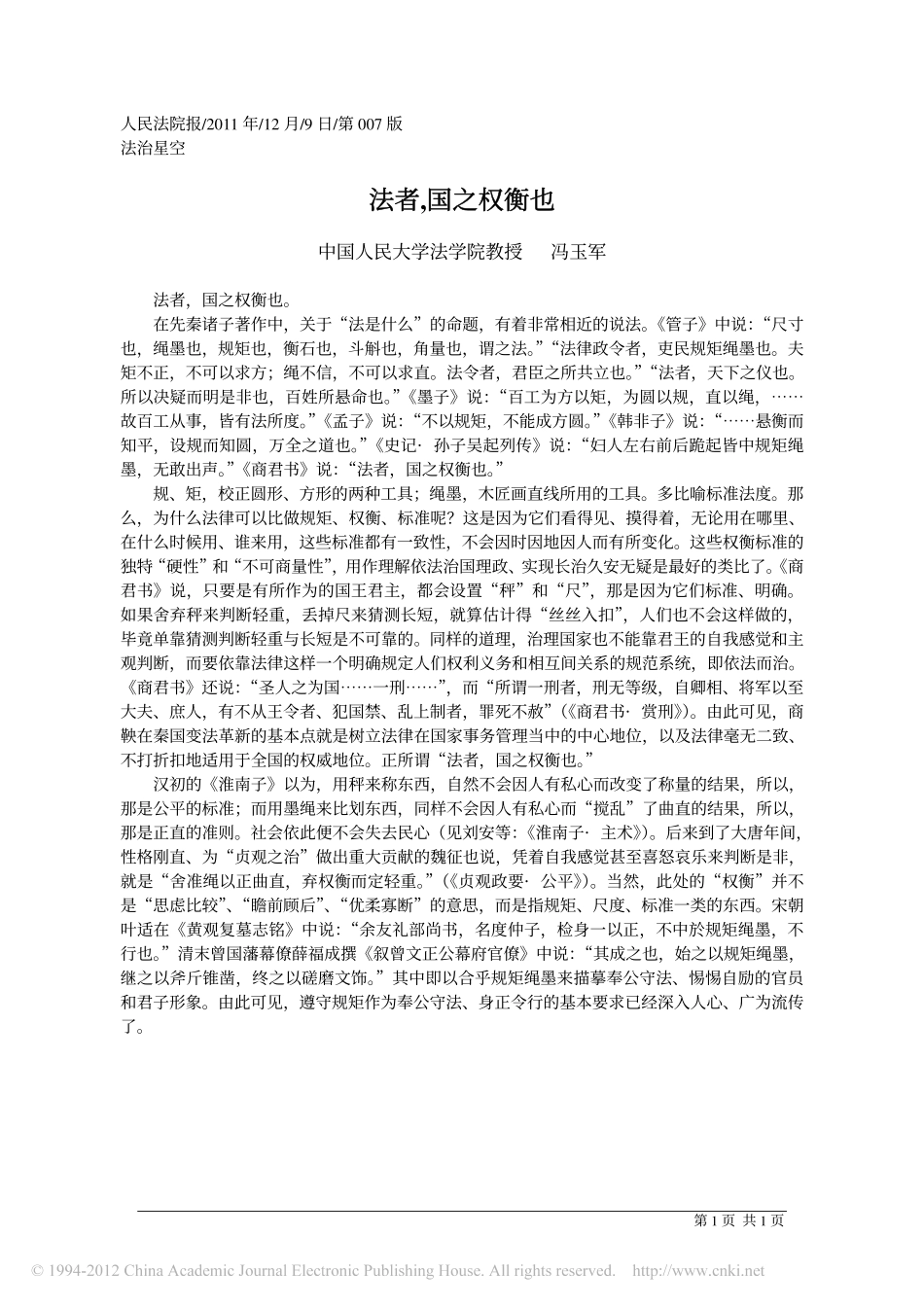第1页共1页人民法院报/2011年/12月/9日/第007版法治星空法者,国之权衡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冯玉军法者,国之权衡也。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关于“法是什么”的命题,有着非常相近的说法。《管子》中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墨子》说:“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孟子》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韩非子》说:“⋯⋯悬衡而知平,设规而知圆,万全之道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商君书》说:“法者,国之权衡也。”规、矩,校正圆形、方形的两种工具;绳墨,木匠画直线所用的工具。多比喻标准法度。那么,为什么法律可以比做规矩、权衡、标准呢?这是因为它们看得见、摸得着,无论用在哪里、在什么时候用、谁来用,这些标准都有一致性,不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变化。这些权衡标准的独特“硬性”和“不可商量性”,用作理解依法治国理政、实现长治久安无疑是最好的类比了。《商君书》说,只要是有所作为的国王君主,都会设置“秤”和“尺”,那是因为它们标准、明确。如果舍弃秤来判断轻重,丢掉尺来猜测长短,就算估计得“丝丝入扣”,人们也不会这样做的,毕竟单靠猜测判断轻重与长短是不可靠的。同样的道理,治理国家也不能靠君王的自我感觉和主观判断,而要依靠法律这样一个明确规定人们权利义务和相互间关系的规范系统,即依法而治。《商君书》还说:“圣人之为国⋯⋯一刑⋯⋯”,而“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者、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由此可见,商鞅在秦国变法革新的基本点就是树立法律在国家事务管理当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法律毫无二致、不打折扣地适用于全国的权威地位。正所谓“法者,国之权衡也。”汉初的《淮南子》以为,用秤来称东西,自然不会因人有私心而改变了称量的结果,所以,那是公平的标准;而用墨绳来比划东西,同样不会因人有私心而“搅乱”了曲直的结果,所以,那是正直的准则。社会依此便不会失去民心(见刘安等:《淮南子·主术》)。后来到了大唐年间,性格刚直、为“贞观之治”做出重大贡献的魏征也说,凭着自我感觉甚至喜怒哀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