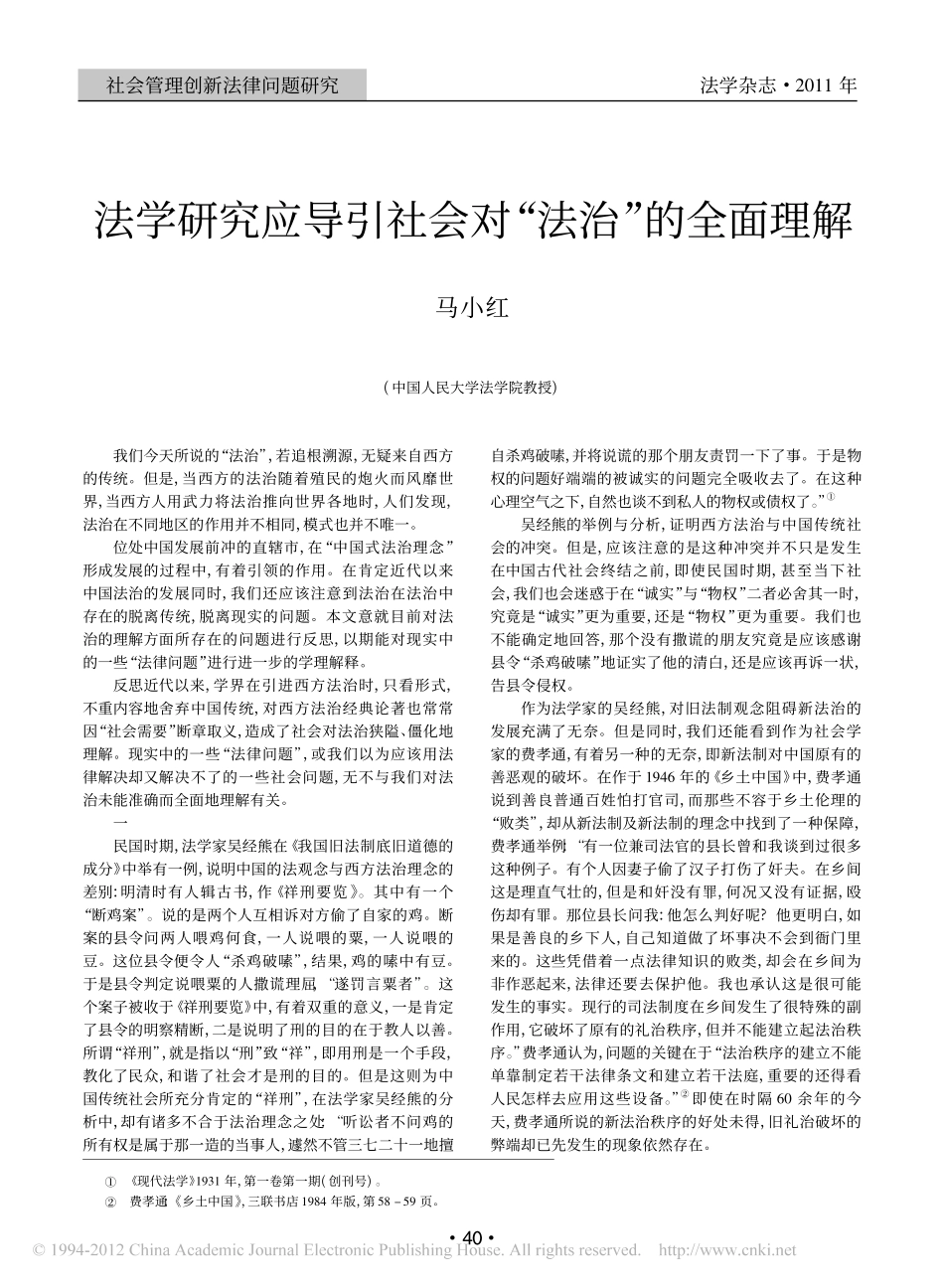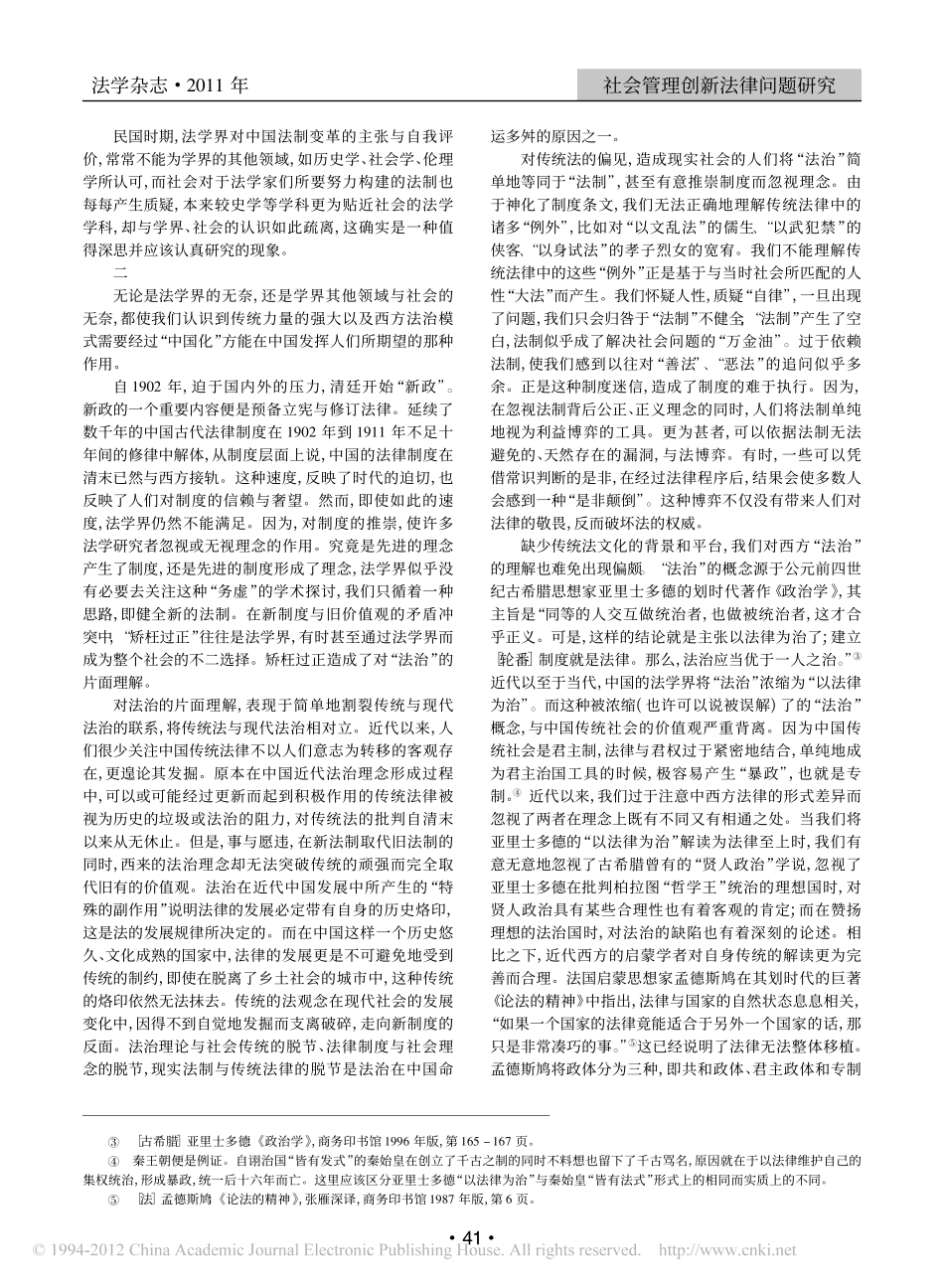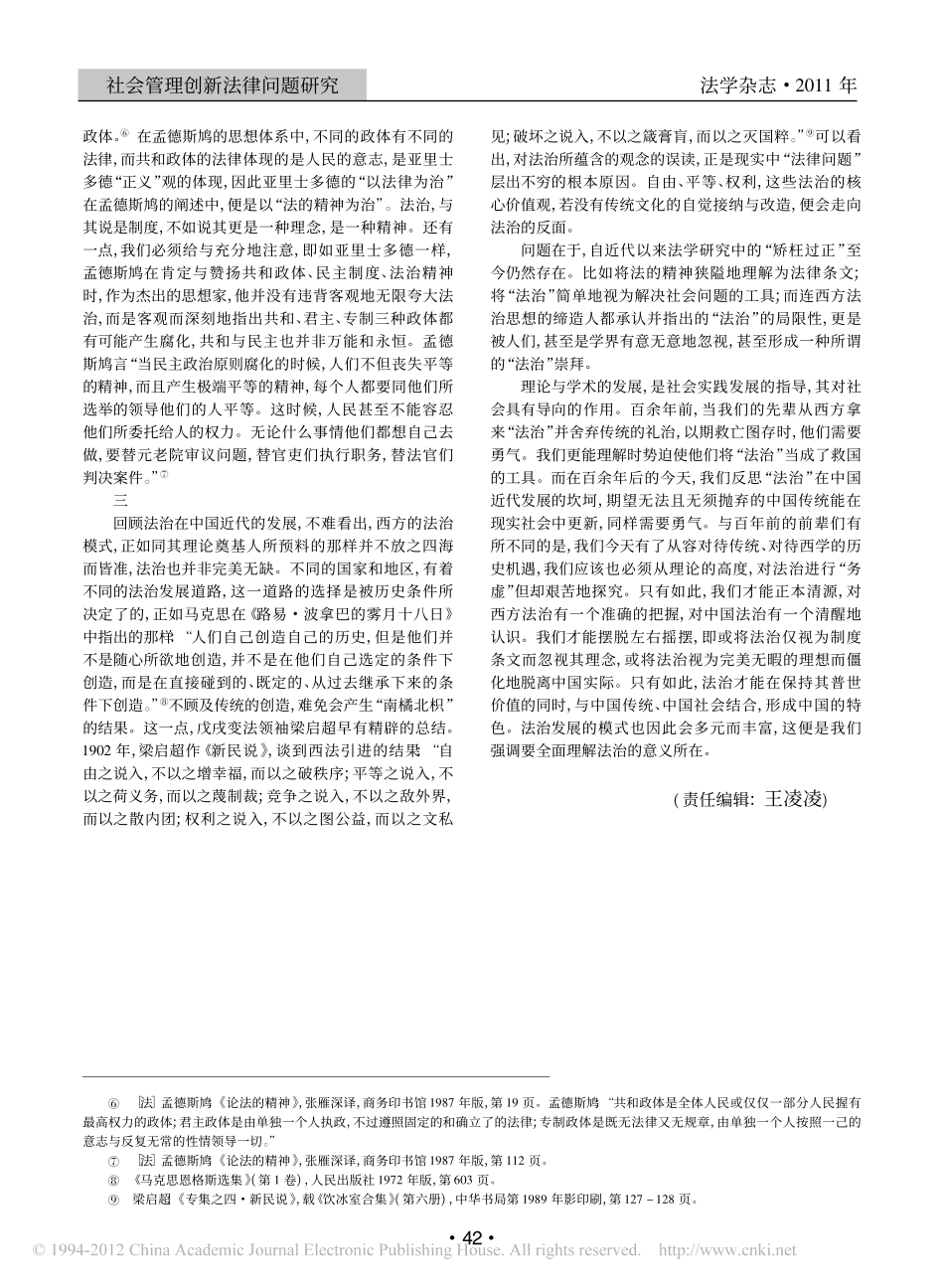社会管理创新法律问题研究法学杂志·2011年①《现代法学》1931年,第一卷第一期(创刊号)。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8-59页。法学研究应导引社会对“法治”的全面理解马小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我们今天所说的“法治”,若追根溯源,无疑来自西方的传统。但是,当西方的法治随着殖民的炮火而风靡世界,当西方人用武力将法治推向世界各地时,人们发现,法治在不同地区的作用并不相同,模式也并不唯一。位处中国发展前冲的直辖市,在“中国式法治理念”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有着引领的作用。在肯定近代以来中国法治的发展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法治在法治中存在的脱离传统,脱离现实的问题。本文意就目前对法治的理解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期能对现实中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学理解释。反思近代以来,学界在引进西方法治时,只看形式,不重内容地舍弃中国传统,对西方法治经典论著也常常因“社会需要”断章取义,造成了社会对法治狭隘、僵化地理解。现实中的一些“法律问题”,或我们以为应该用法律解决却又解决不了的一些社会问题,无不与我们对法治未能准确而全面地理解有关。一民国时期,法学家吴经熊在《我国旧法制底旧道德的成分》中举有一例,说明中国的法观念与西方法治理念的差别:明清时有人辑古书,作《祥刑要览》。其中有一个“断鸡案”。说的是两个人互相诉对方偷了自家的鸡。断案的县令问两人喂鸡何食,一人说喂的粟,一人说喂的豆。这位县令便令人“杀鸡破嗉”,结果,鸡的嗉中有豆。于是县令判定说喂粟的人撒谎理屈,“遂罚言粟者”。这个案子被收于《祥刑要览》中,有着双重的意义,一是肯定了县令的明察精断,二是说明了刑的目的在于教人以善。所谓“祥刑”,就是指以“刑”致“祥”,即用刑是一个手段,教化了民众,和谐了社会才是刑的目的。但是这则为中国传统社会所充分肯定的“祥刑”,在法学家吴经熊的分析中,却有诸多不合于法治理念之处:“听讼者不问鸡的所有权是属于那一造的当事人,遽然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擅自杀鸡破嗉,并将说谎的那个朋友责罚一下了事。于是物权的问题好端端的被诚实的问题完全吸收去了。在这种心理空气之下,自然也谈不到私人的物权或债权了。”①吴经熊的举例与分析,证明西方法治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冲突。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冲突并不只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终结之前,即使民国时期,甚至当下社会,我们也会迷惑于在“诚实”与“物权”二者必舍其一时,究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