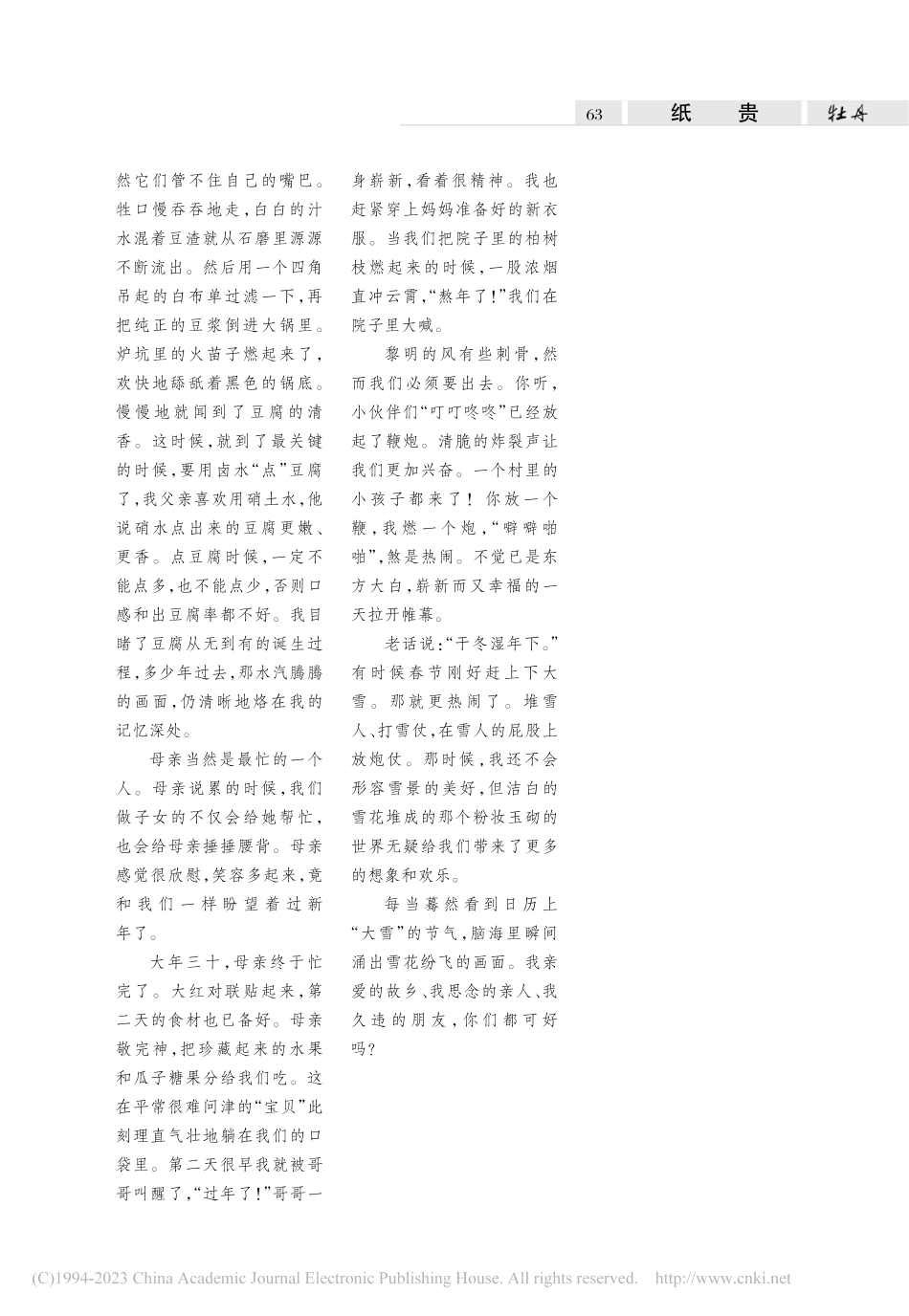纸贵来。这个办法简便实用,需要就地取材用石头铺垫一条人工挑水的“码头”。“码头”长约十余米,宽约一米,从河边一直延伸到深水处,挑水的人直接经过“码头”便能轻松地将水桶汲满,然后轻松地上岸,径直将水挑回家去。这样的“码头”一年四季都存在,冲毁了再建,建了再冲毁,循环往复。为了汲水,古镇人啥苦都能吃,啥困难都不怕。每年的汛期,河水浑浊,会在河边的沙滩上挖一个大坑,用光滑干净的鹅卵石垫底,四周用石块堆砌,浑浊的河水经过沙石过滤,变得清亮亮满当当的。这种沙窝井只是临时救急用的,只要河水返清,便弃之不用。仿佛在古镇人心里,只有下河挑水才觉得亲切踏实。我上初中时就开始下河担水。我喜欢担水是想赢得母亲的称赞。每次担水回家,母亲总是笑眯眯的,总是爱怜地对我说:“水莫挑太满,莫着急,多歇几气,悠和着挑。人一辈子是挑不完水的。”母亲越是这样说,我越是把水桶装得盈溢,越是一路不停歇,直到把那口大水缸挑满为止。时代迅猛发展,如今挑水已成为历史而封尘在记忆中,而我始终忘不了担水过日子的往昔岁月。因为我在担水中不断成长,我走出任河在汉江边一座美丽的山城生活和工作,每天看见任河水与汉江交融,总感觉任河水里有我的影子,有古镇人担水的影子,虽然古镇上的人大多进了县城,甚至是到了比县城更远的城市生活,但他们如同滔滔任河水涌进母亲河汉江一样,流得越远,对故乡的思念就会越深越浓,直到人最终也化成了水,回到故乡任河水的怀抱。日子一进入腊月,便如快马加鞭一样令人心生感慨。然而小时候可是天天巴望着快点儿过年,新年到,穿新衣,放花炮,不干啥,吃得好。过了阴历腊月二十就开始忙活了。母亲蒸馍、煮肉、炸馃子,父亲泡豆子、磨豆腐、割肉,我们小孩子也有事做,砍柏枝、烧火,跟着父亲去刮硝土。那时候日子是紧巴,可再穷也要过个好年。又是宰鸡子,又是杀年猪。可村里会杀猪的两三个人,要数老赵杀得最娴熟。老赵光头,肥肥的,个头也不高。每年杀年猪的时候,旁边既有帮工,也有看客,很是热闹。猪却非常恐慌,它好像也知道生命将到尽头,扯着绳子就是不愿往前走。有人打一棍子,它就扯着嗓子撕心裂肺地嚎。老赵却丝毫也不手软,举起棍子就是当头一棒,猪立刻昏头昏脑了,四脚踢腾着被抬到了案板上。老赵拿刀对着猪脖子噗嗤就是一下,殷红而粘稠的猪血就流到了盆子里。纯净的猪血被几家人拿回家浸煮成血块,过年放在凉粉汤里,鲜嫩可口。那时我们村子虽小,人情味却很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