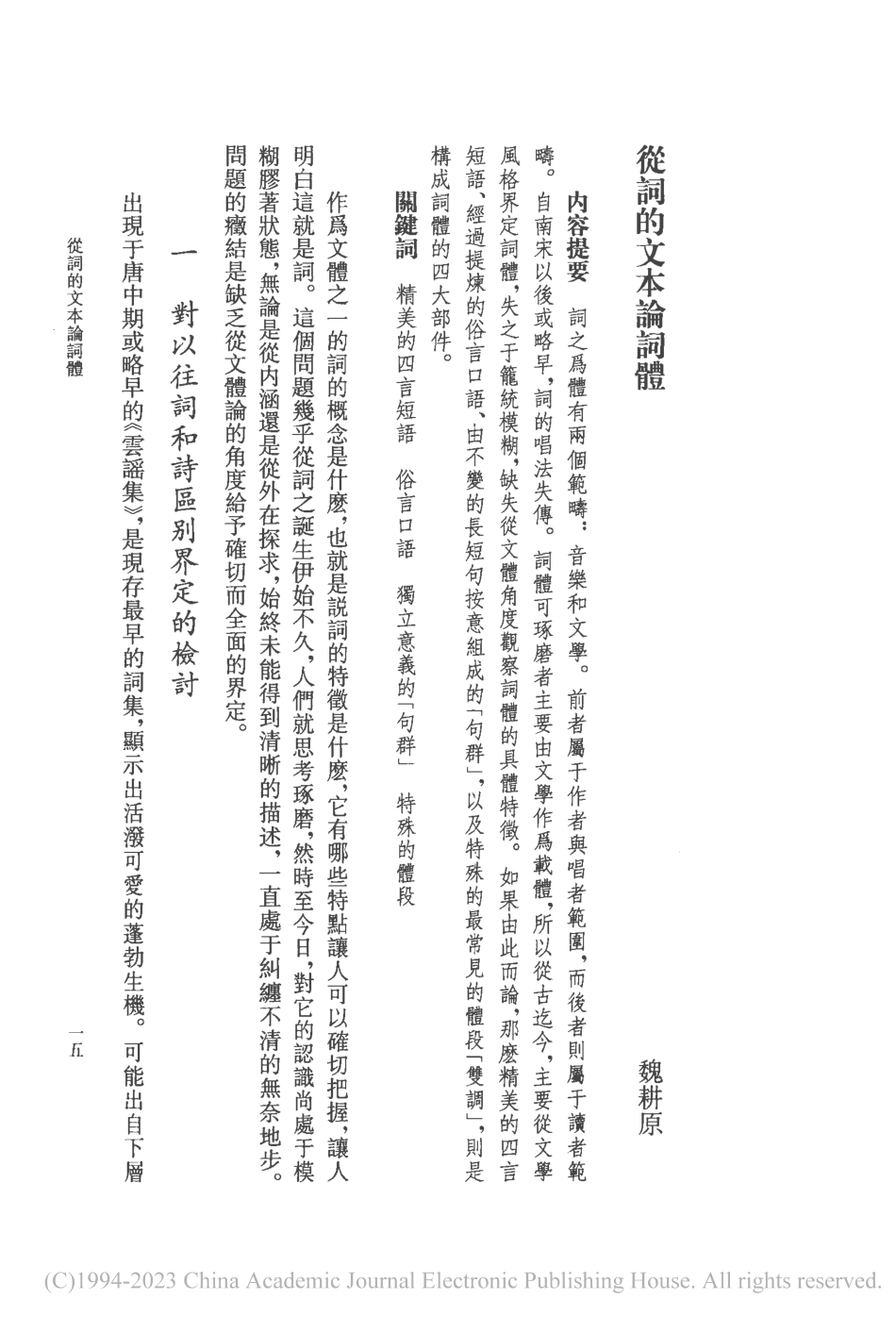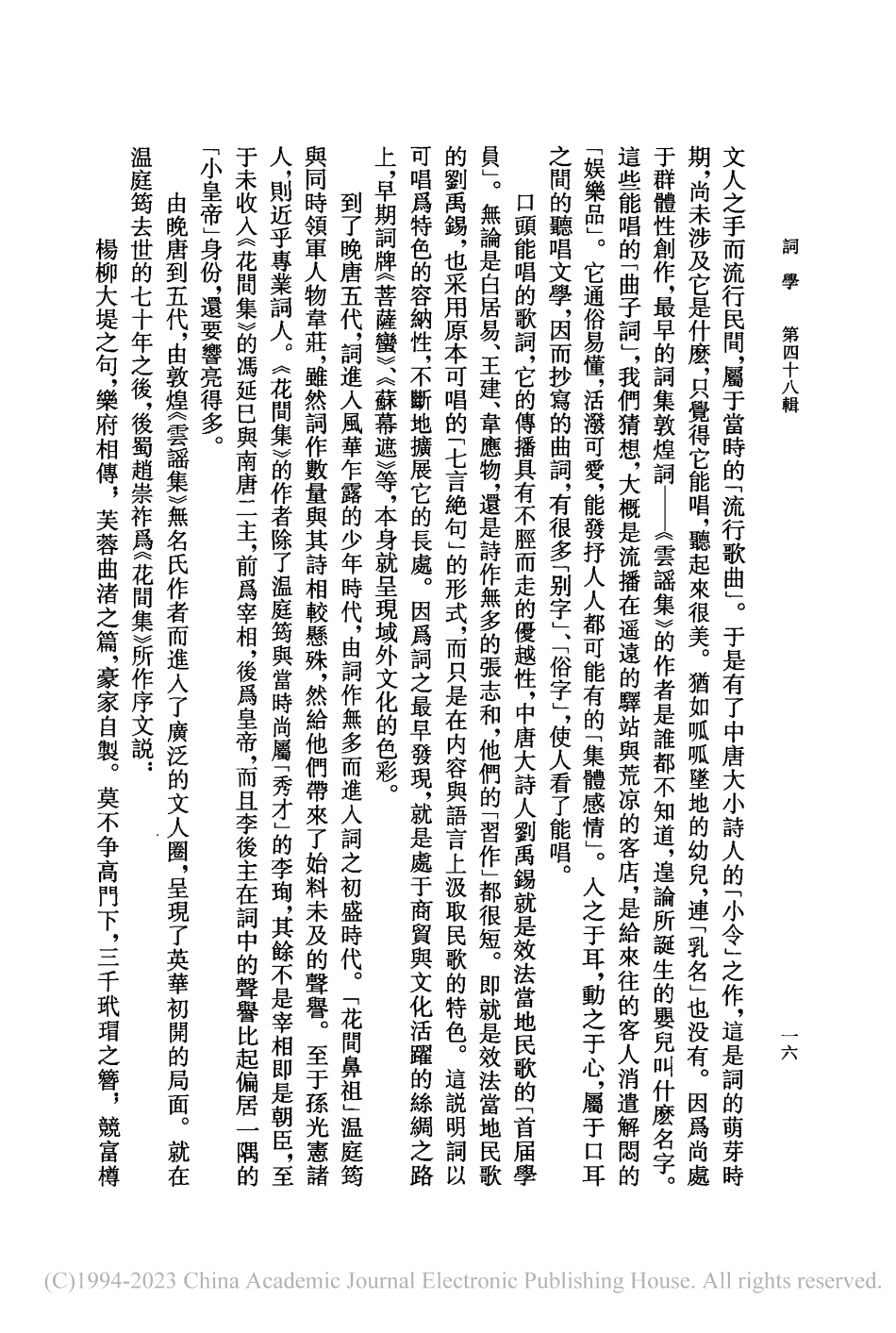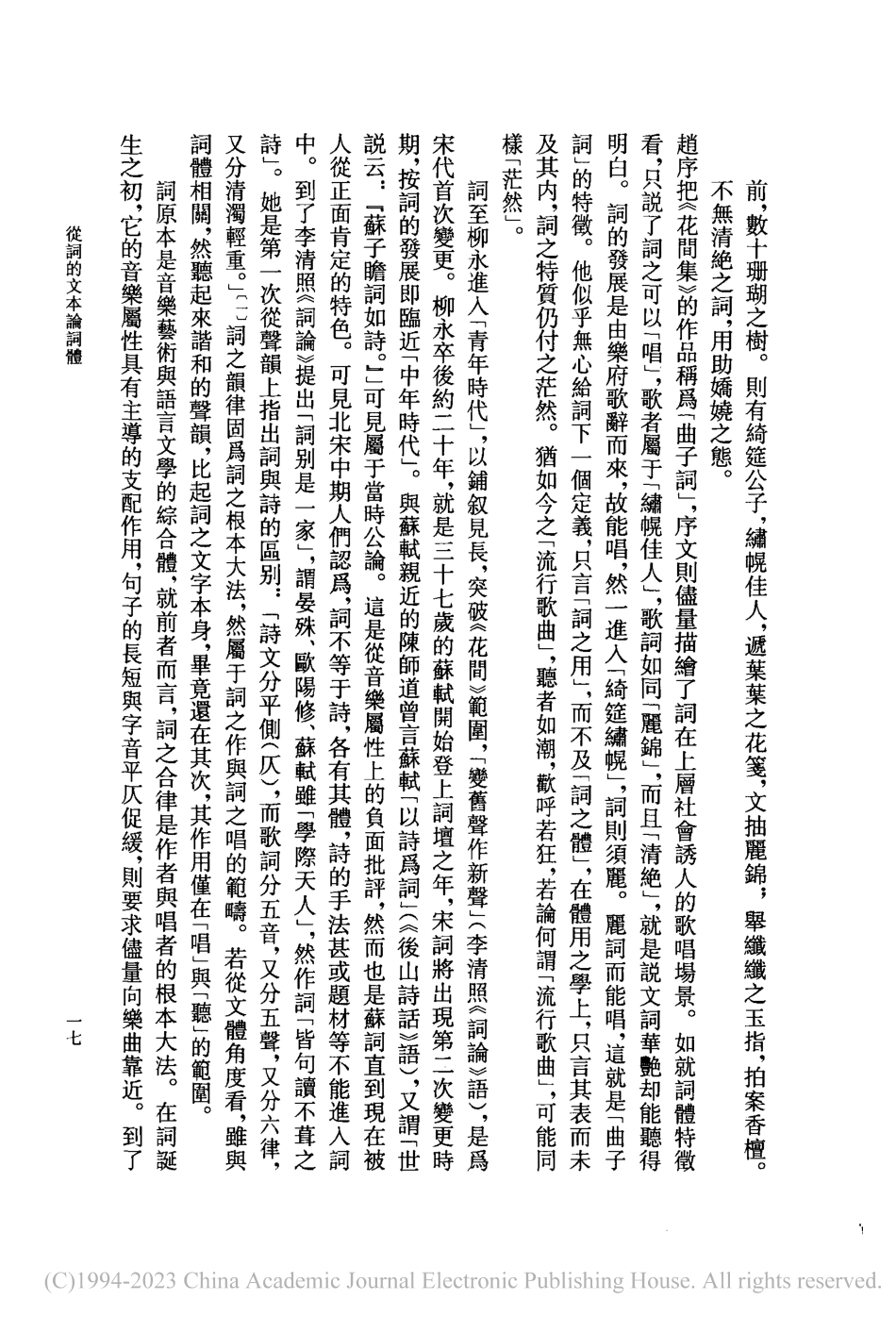從詞的文本論詞體魏耕原内容提要詞之爲體有兩個範疇:音樂和文學。前者屬于作者與唱者範圍,而後者則屬于讀者範疇。自南宋以後或略早,詞的唱法失傳。詞體可琢磨者主要由文學作爲载體,所以從古迄今,主要從文學風格界定詞體,失之于籠統模糊,缺失從文體角度觀察詞體的具體特徵。如果由此而論,那麽精美的四言短語、經過提煉的俗言口語、由不變的長短句按意組成的「句群」,以及特殊的最常見的體段「雙調」,則是構成詞體的四大部件。關鍵詞精美的四言短語俗言口語獨立意義的「句群」特殊的體段作爲文體之一的詞的概念是什麽,也就是説詞的特徵是什麽,它有哪些特點讓人可以確切把握,讓人明白這就是詞。這個問題幾乎從詞之誕生伊始不久,人們就思考琢磨,然時至今日,對它的認識尚處于模糊膠著狀態,無論是從内涵還是從外在探求,始終未能得到清晰的描述,一直處于糾纏不清的無奈地步。問題的癥結是缺乏從文體論的角度給予確切而全面的界定。一對以往詞和詩區别界定的檢討出現于唐中期或略早的《雲謡集》,是現存最早的詞集,顯示出活潑可愛的蓬勃生機。可能出自下層從詞的文本論詞體一五詞學第四十八輯一六文人之手而流行民間,屬于當時的「流行歌曲」。于是有了中唐大小詩人的「小令」之作,這是詞的萌芽時期,尚未涉及它是什麽,只覺得它能唱,聽起來很美。猶如呱呱墜地的幼兒,連「乳名」也没有。因爲尚處于群體性創作,最早的詞集敦煌詞《雲謡集》的作者是誰都不知道,遑論所誕生的嬰兒叫什麽名字。這些能唱的「曲子詞」,我們猜想,大概是流播在遥遠的驛站與荒凉的客店,是給來往的客人消遣解悶的「娱樂品」。它通俗易懂,活潑可愛,能發抒人人都可能有的「集體感情」。人之于耳,動之于心,屬于口耳之間的聽唱文學,因而抄寫的曲詞,有很多「别字」、「俗字」,使人看了能唱。口頭能唱的歌詞,它的傳播具有不脛而走的優越性,中唐大詩人劉禹錫就是效法當地民歌的「首届學員」。無論是白居易、王建、韋應物,還是詩作無多的張志和,他們的「習作」都很短。即就是效法當地民歌的劉禹錫,也采用原本可唱的「七言絶句」的形式,而只是在内容與語言上汲取民歌的特色。這説明詞以可唱爲特色的容納性,不斷地擴展它的長處。因爲詞之最早發現,就是處于商貿與文化活躍的絲綢之路上,早期詞牌《菩薩蠻》、《蘇幕遮》等,本身就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