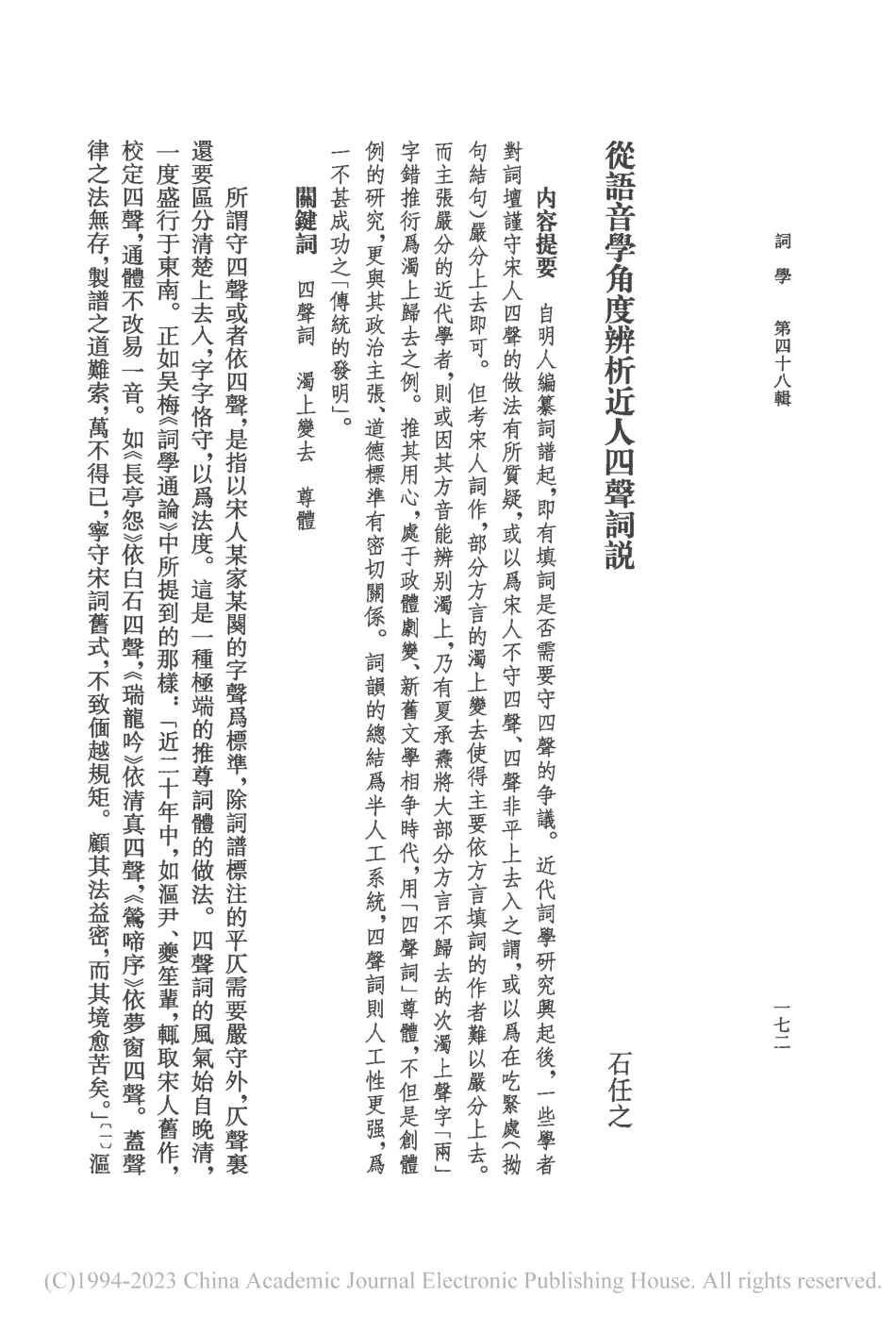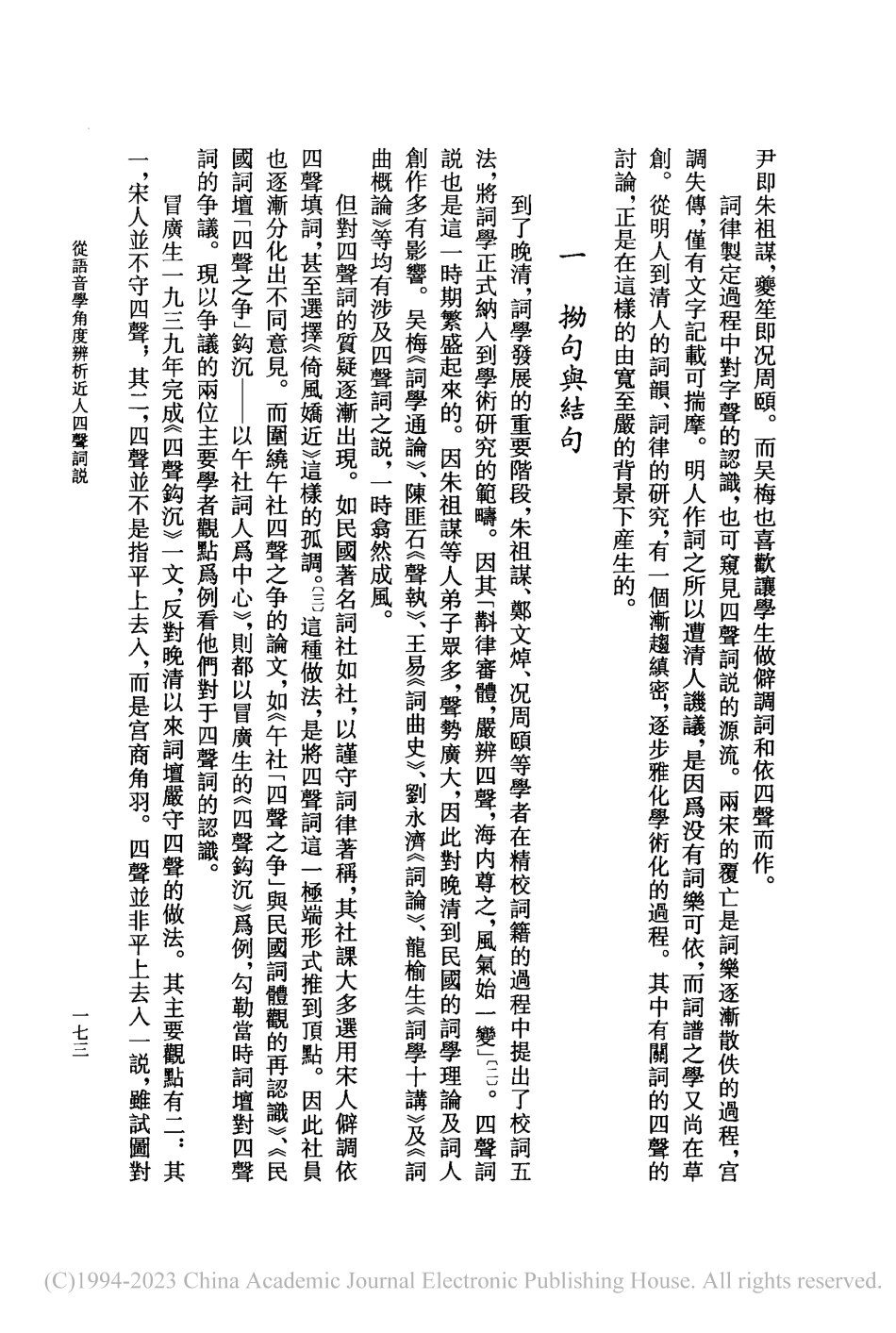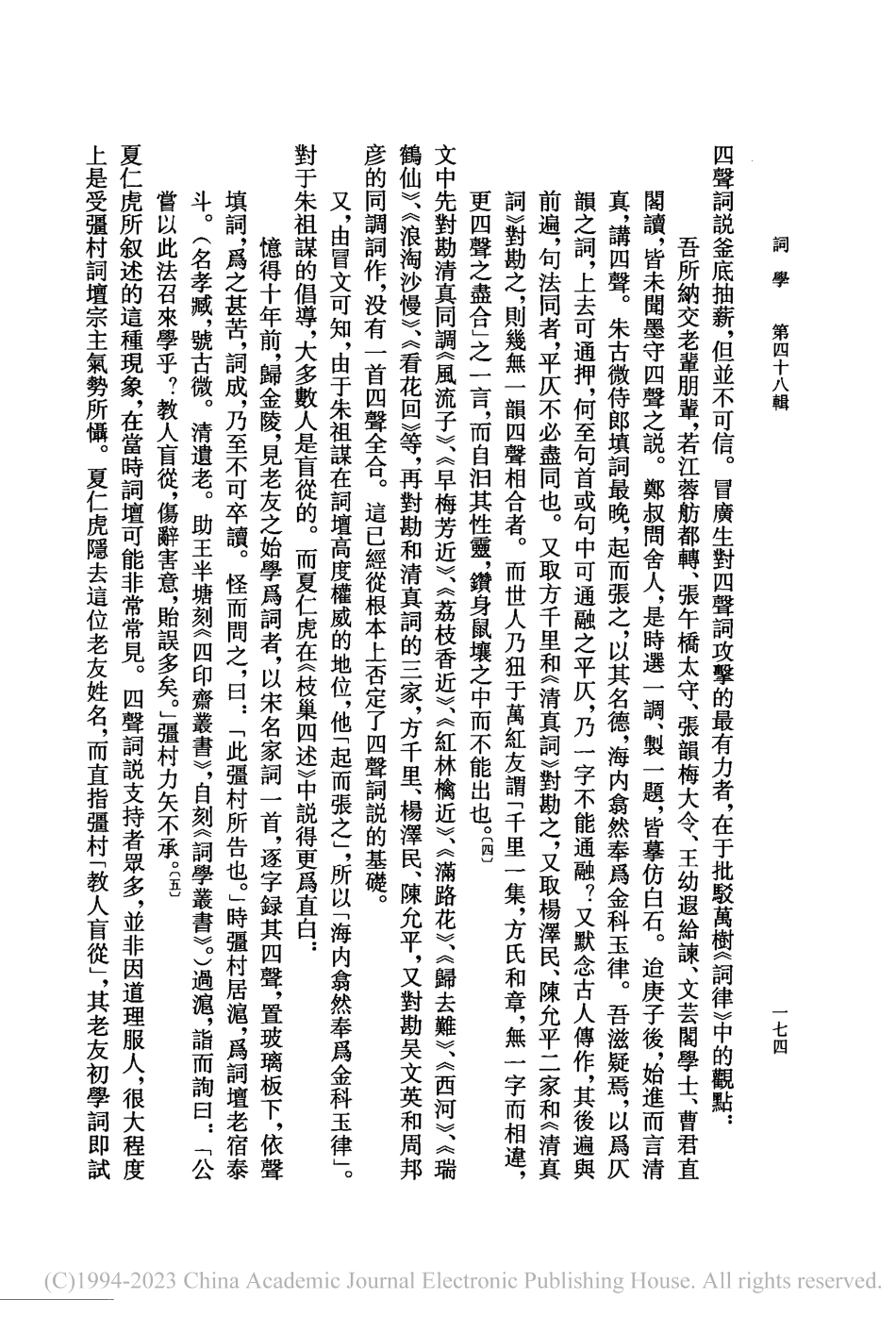詞學第四十八輯一七二從語音學角度辨析近人四聲詞説石任之内容提要自明人編纂詞譜起,即有填詞是否需要守四聲的争議。近代詞學研究興起後,一些學者對詞壇謹守宋人四聲的做法有所質疑,或以爲宋人不守四聲、四聲非平上去入之謂,或以爲在吃緊處(拗句結句)嚴分上去即可。但考宋人詞作,部分方言的濁上變去使得主要依方言填詞的作者難以嚴分上去。而主張嚴分的近代學者,則或因其方音能辨别濁上,乃有夏承燾將大部分方言不歸去的次濁上聲字「兩」字錯推衍爲濁上歸去之例。推其用心,處于政體劇變、新舊文學相争時代,用「四聲詞」尊體,不但是創體例的研究,更與其政治主張、道德標準有密切關係。詞韻的總結爲半人工系統,四聲詞則人工性更强,爲一不甚成功之「傳統的發明」。關鍵詞四聲詞濁上變去尊體所謂守四聲或者依四聲,是指以宋人某家某闋的字聲爲標準,除詞譜標注的平仄需要嚴守外,仄聲裏還要區分清楚上去人,字字恪守,以爲法度。這是一種極端的推尊詞體的做法。四聲詞的風氣始自晚清,一度盛行于東南。正如吴梅《詞學通論》中所提到的那樣:「近二十年中,如滙尹、夔笙輩,輒取宋人舊作,校定四聲,通體不改易一音。如《長亭怨》依白石四聲,《瑞龍吟》依清真四聲,《鶯啼序》依夢窗四聲。蓋聲律之法無存,製譜之道難索,萬不得已,寧守宋詞舊式,不致偭越規矩。顧其法益密,而其境愈苦矣。尹即朱祖謀,夔笙即况周頤。而吴梅也喜歡讓學生做僻調詞和依四聲而作。詞律製定過程中對字聲的認識,也可窺見四聲詞説的源流。兩宋的覆亡是詞樂逐漸散佚的過程,宫調失傳,僅有文字記載可揣摩。明人作詞之所以遭清人譏議,是因爲没有詞樂可依,而詞譜之學又尚在草創。從明人到清人的詞韻、詞律的研究,有一個漸趨縝密,逐步雅化學術化的過程。其中有關詞的四聲的討論,正是在這樣的由寬至嚴的背景下産生的。一拗句與結句到了晚清,詞學發展的重要階段,朱祖謀、鄭文焯、况周頤等學者在精校詞籍的過程中提出了校詞五法,將詞學正式納人到學術研究的範疇。因其「斛律審體,嚴辨四聲,海内尊之,風氣始一變」〔5。四聲詞説也是這一時期繁盛起來的。因朱祖謀等人弟子眾多,聲勢廣大,因此對晚清到民國的詞學理論及詞人創作多有影響。吴梅《詞學通論》、陳匪石《聲執》、王易《詞曲史》、劉永濟《詞論》、龍榆生《詞學十講》及《詞曲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