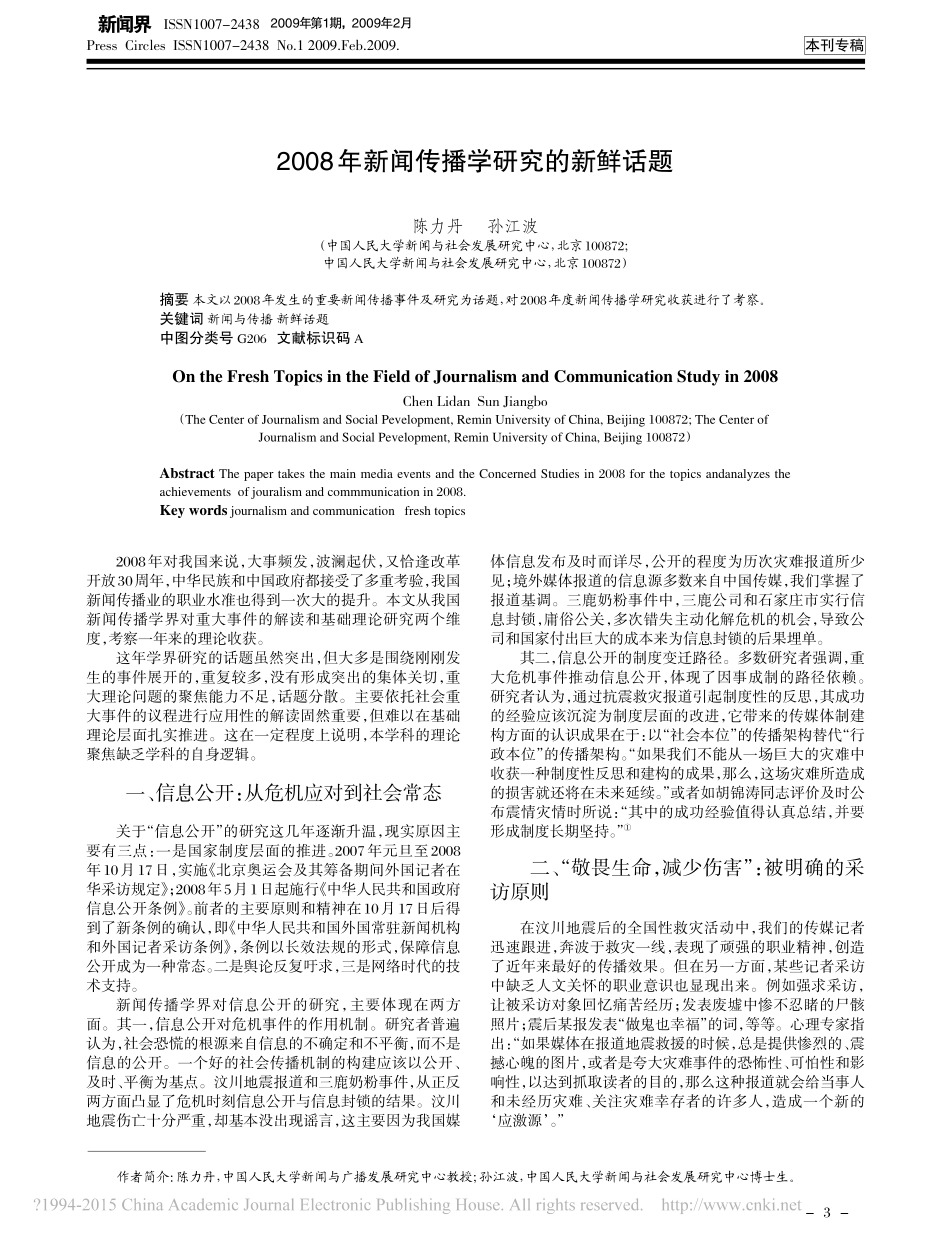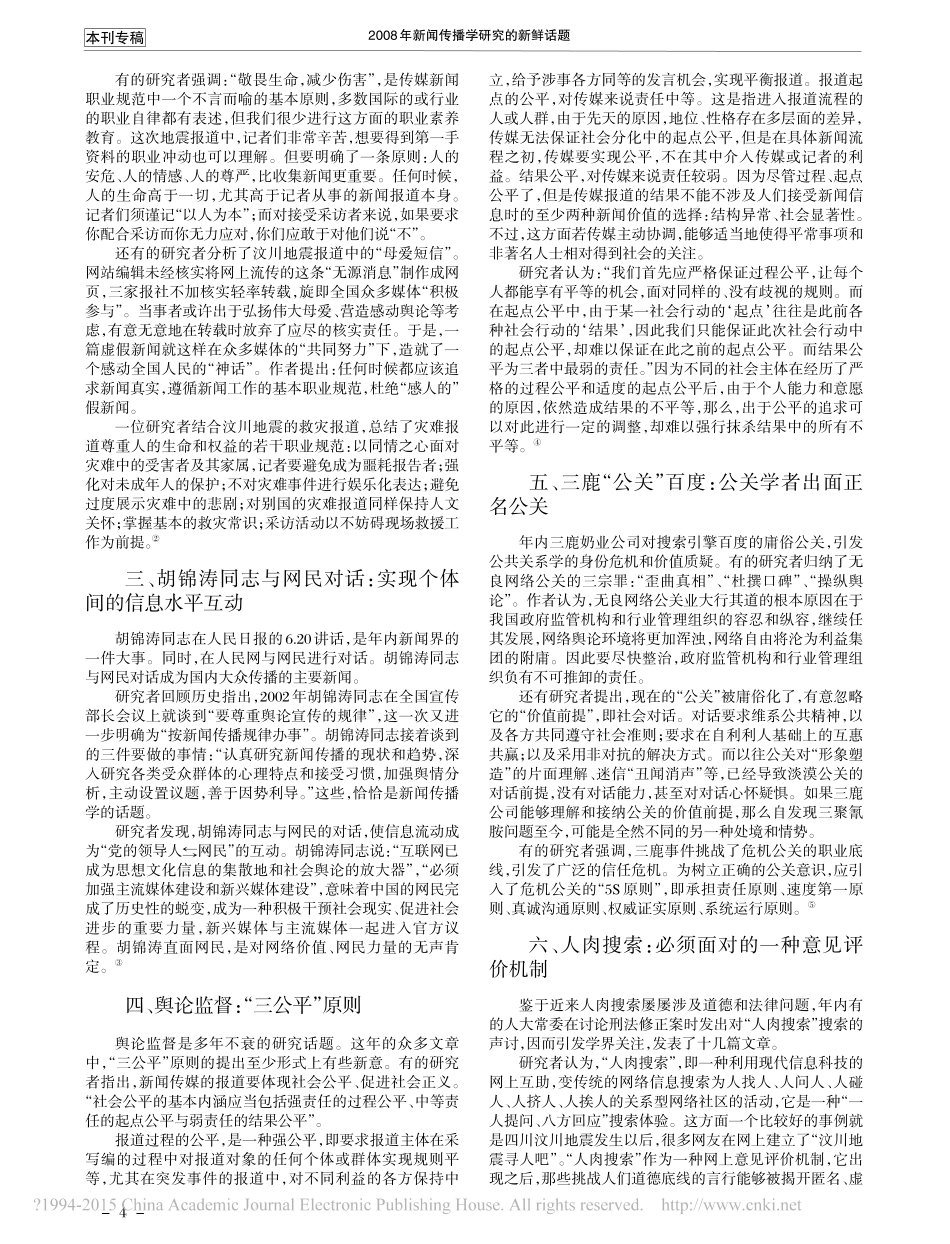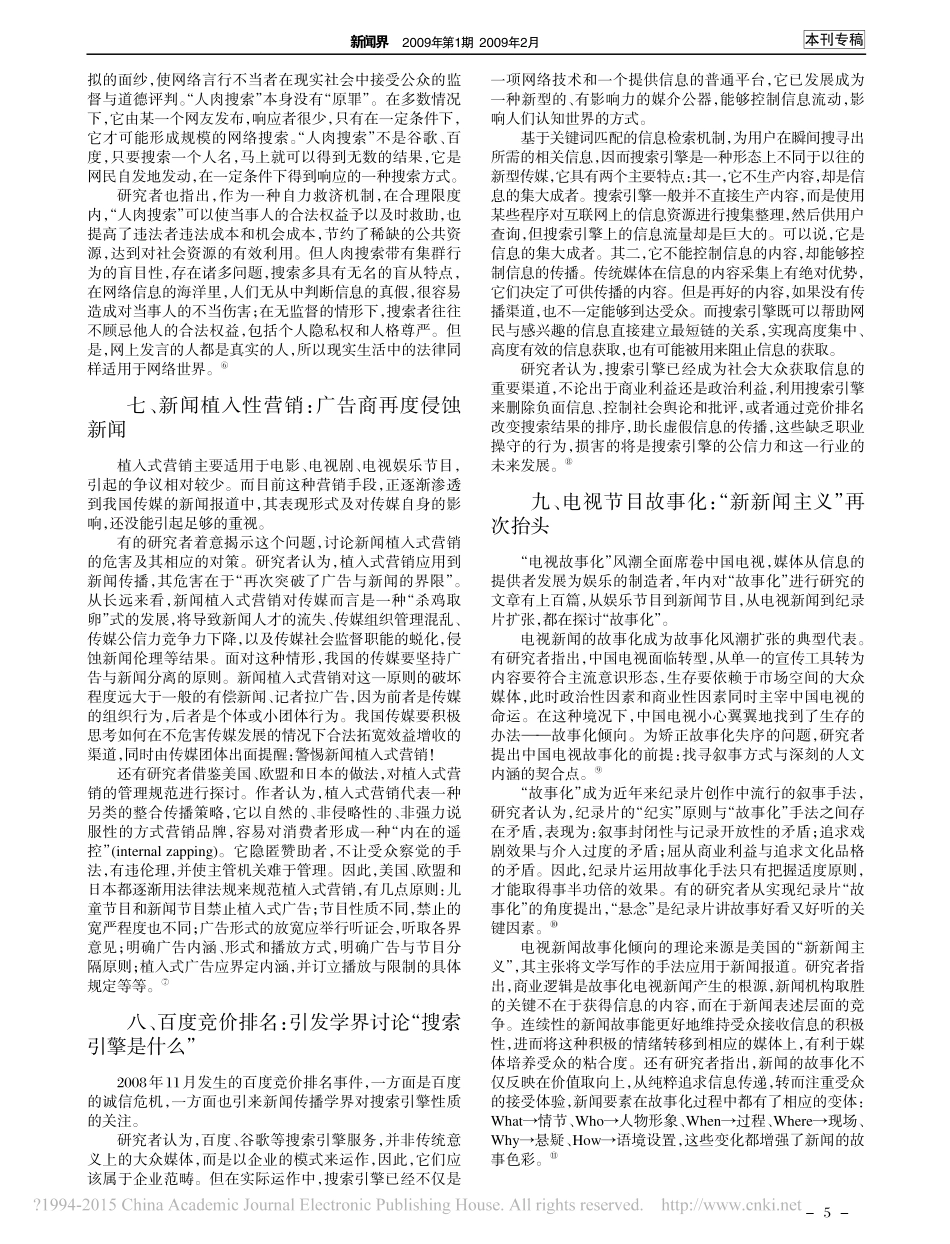2008年对我国来说,大事频发,波澜起伏,又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中华民族和中国政府都接受了多重考验,我国新闻传播业的职业水准也得到一次大的提升。本文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对重大事件的解读和基础理论研究两个维度,考察一年来的理论收获。这年学界研究的话题虽然突出,但大多是围绕刚刚发生的事件展开的,重复较多,没有形成突出的集体关切,重大理论问题的聚焦能力不足,话题分散。主要依托社会重大事件的议程进行应用性的解读固然重要,但难以在基础理论层面扎实推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学科的理论聚焦缺乏学科的自身逻辑。一、信息公开:从危机应对到社会常态关于“信息公开”的研究这几年逐渐升温,现实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国家制度层面的推进。2007年元旦至2008年10月17日,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2008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前者的主要原则和精神在10月17日后得到了新条例的确认,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条例以长效法规的形式,保障信息公开成为一种常态。二是舆论反复吁求,三是网络时代的技术支持。新闻传播学界对信息公开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信息公开对危机事件的作用机制。研究者普遍认为,社会恐慌的根源来自信息的不确定和不平衡,而不是信息的公开。一个好的社会传播机制的构建应该以公开、及时、平衡为基点。汶川地震报道和三鹿奶粉事件,从正反两方面凸显了危机时刻信息公开与信息封锁的结果。汶川地震伤亡十分严重,却基本没出现谣言,这主要因为我国媒体信息发布及时而详尽,公开的程度为历次灾难报道所少见;境外媒体报道的信息源多数来自中国传媒,我们掌握了报道基调。三鹿奶粉事件中,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实行信息封锁,庸俗公关,多次错失主动化解危机的机会,导致公司和国家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为信息封锁的后果埋单。其二,信息公开的制度变迁路径。多数研究者强调,重大危机事件推动信息公开,体现了因事成制的路径依赖。研究者认为,通过抗震救灾报道引起制度性的反思,其成功的经验应该沉淀为制度层面的改进,它带来的传媒体制建构方面的认识成果在于:以“社会本位”的传播架构替代“行政本位”的传播架构。“如果我们不能从一场巨大的灾难中收获一种制度性反思和建构的成果,那么,这场灾难所造成的损害就还将在未来延续。”或者如胡锦涛同志评价及时公布震情灾情时所说:“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