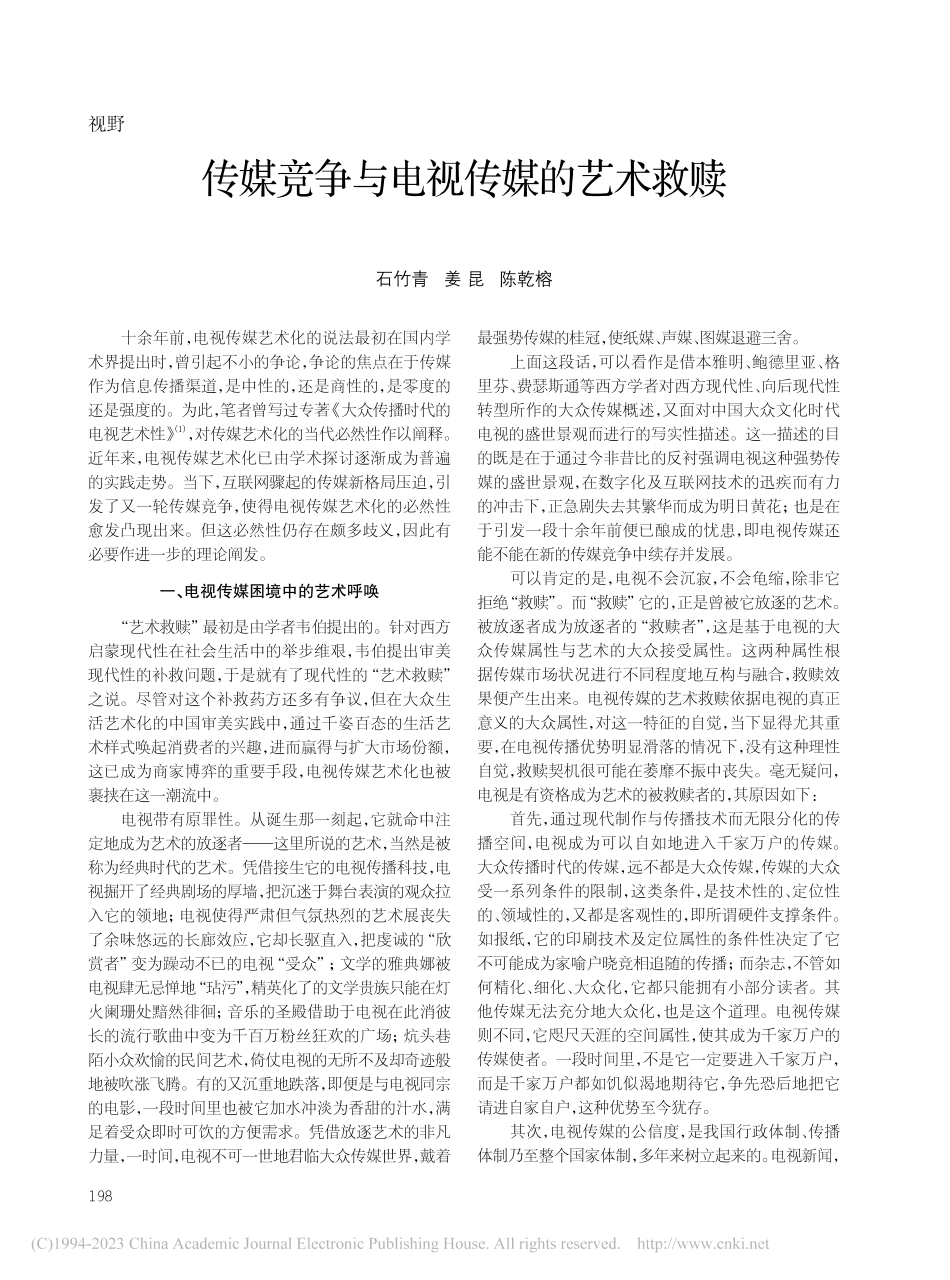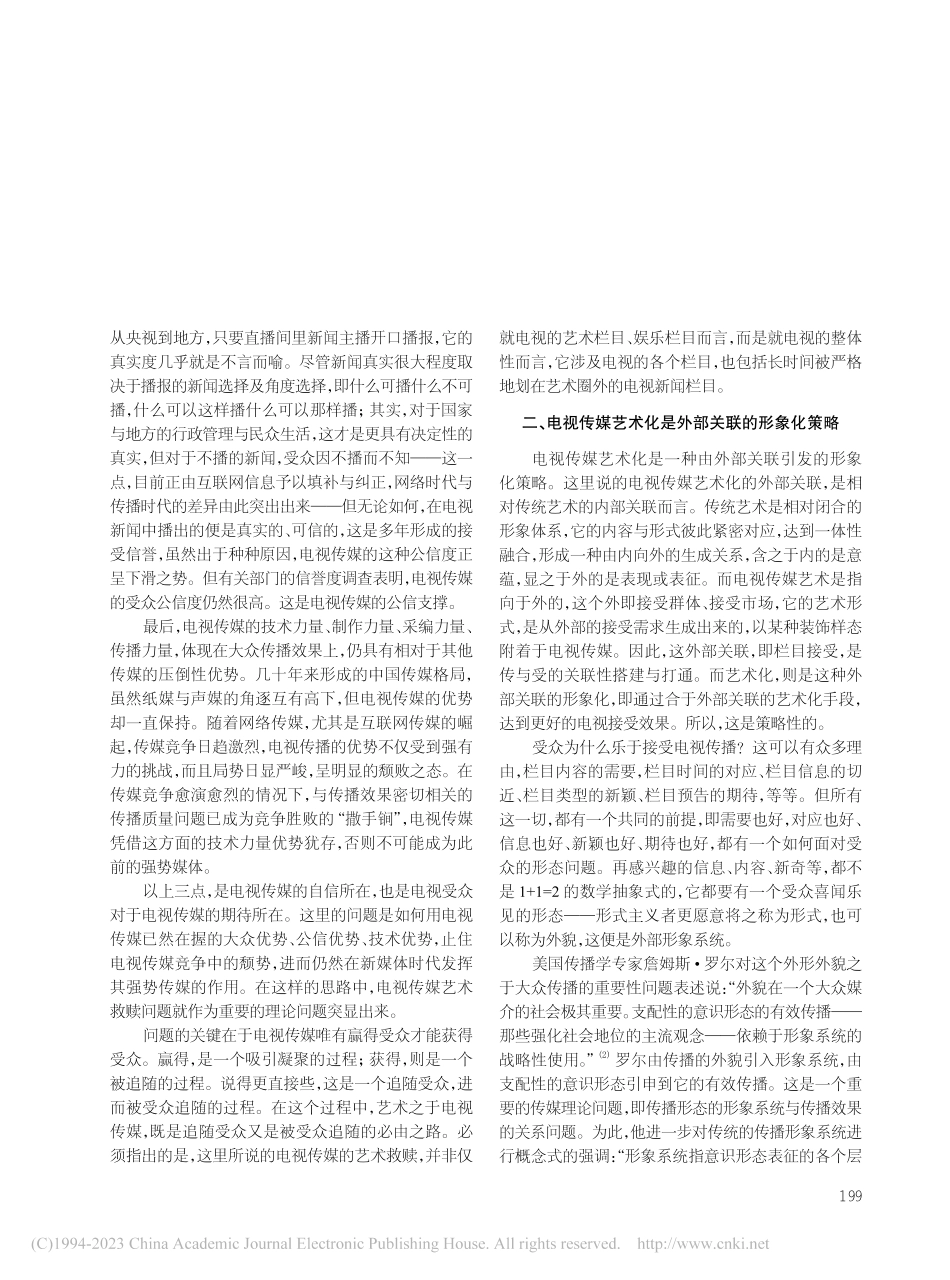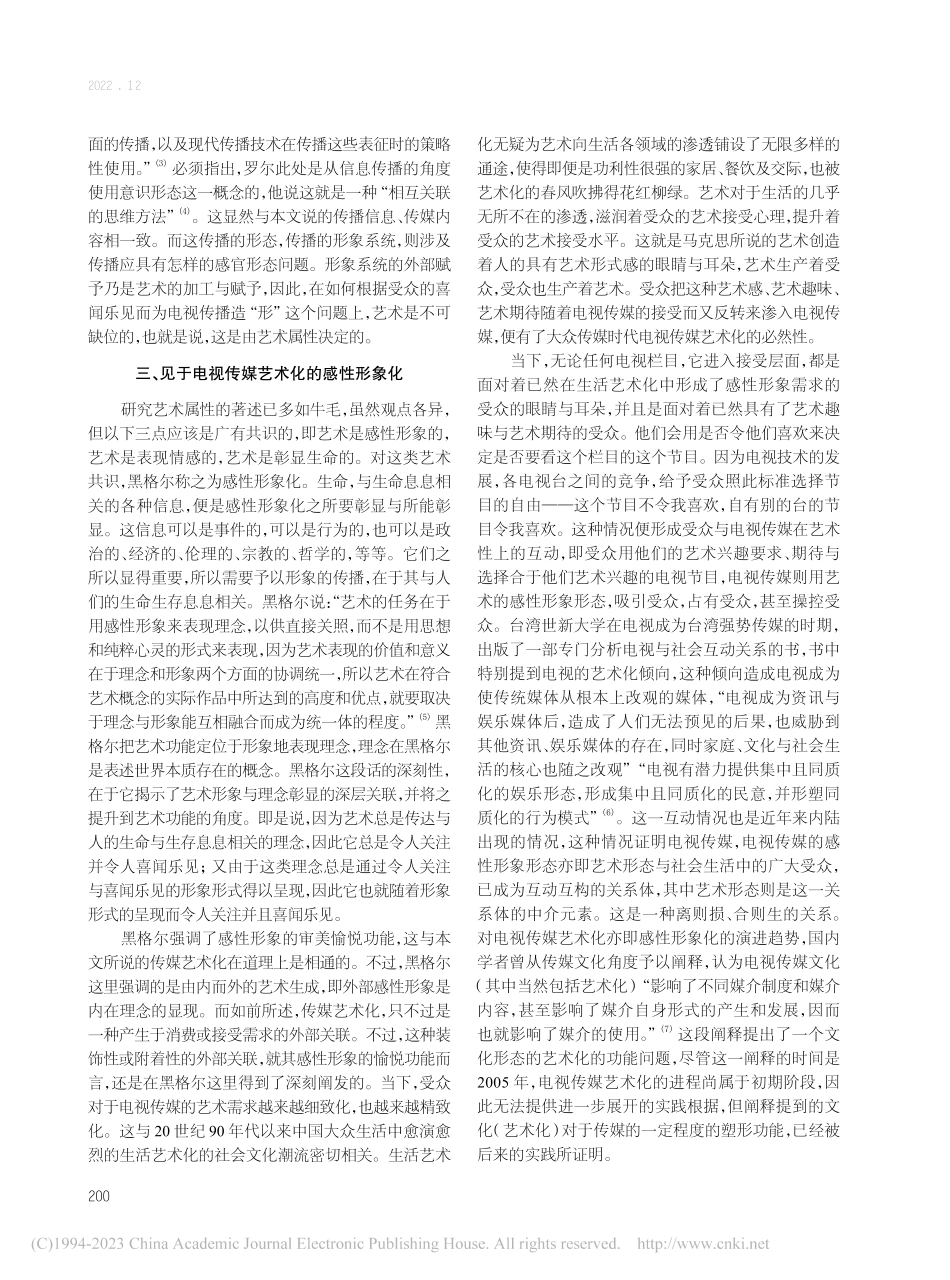十余年前,电视传媒艺术化的说法最初在国内学术界提出时,曾引起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传媒作为信息传播渠道,是中性的,还是商性的,是零度的还是强度的。为此,笔者曾写过专著《大众传播时代的电视艺术性》(1),对传媒艺术化的当代必然性作以阐释。近年来,电视传媒艺术化已由学术探讨逐渐成为普遍的实践走势。当下,互联网骤起的传媒新格局压迫,引发了又一轮传媒竞争,使得电视传媒艺术化的必然性愈发凸现出来。但这必然性仍存在颇多歧义,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理论阐发。一、电视传媒困境中的艺术呼唤“艺术救赎”最初是由学者韦伯提出的。针对西方启蒙现代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举步维艰,韦伯提出审美现代性的补救问题,于是就有了现代性的“艺术救赎”之说。尽管对这个补救药方还多有争议,但在大众生活艺术化的中国审美实践中,通过千姿百态的生活艺术样式唤起消费者的兴趣,进而赢得与扩大市场份额,这已成为商家博弈的重要手段,电视传媒艺术化也被裹挟在这一潮流中。电视带有原罪性。从诞生那一刻起,它就命中注定地成为艺术的放逐者——这里所说的艺术,当然是被称为经典时代的艺术。凭借接生它的电视传播科技,电视掘开了经典剧场的厚墙,把沉迷于舞台表演的观众拉入它的领地;电视使得严肃但气氛热烈的艺术展丧失了余味悠远的长廊效应,它却长驱直入,把虔诚的“欣赏者”变为躁动不已的电视“受众”;文学的雅典娜被电视肆无忌惮地“玷污”,精英化了的文学贵族只能在灯火阑珊处黯然徘徊;音乐的圣殿借助于电视在此消彼长的流行歌曲中变为千百万粉丝狂欢的广场;炕头巷陌小众欢愉的民间艺术,倚仗电视的无所不及却奇迹般地被吹涨飞腾。有的又沉重地跌落,即便是与电视同宗的电影,一段时间里也被它加水冲淡为香甜的汁水,满足着受众即时可饮的方便需求。凭借放逐艺术的非凡力量,一时间,电视不可一世地君临大众传媒世界,戴着最强势传媒的桂冠,使纸媒、声媒、图媒退避三舍。上面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借本雅明、鲍德里亚、格里芬、费瑟斯通等西方学者对西方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型所作的大众传媒概述,又面对中国大众文化时代电视的盛世景观而进行的写实性描述。这一描述的目的既是在于通过今非昔比的反衬强调电视这种强势传媒的盛世景观,在数字化及互联网技术的迅疾而有力的冲击下,正急剧失去其繁华而成为明日黄花;也是在于引发一段十余年前便已酿成的忧患,即电视传媒还能不能在新的传媒竞争中续存并发展。可以肯定的是,电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