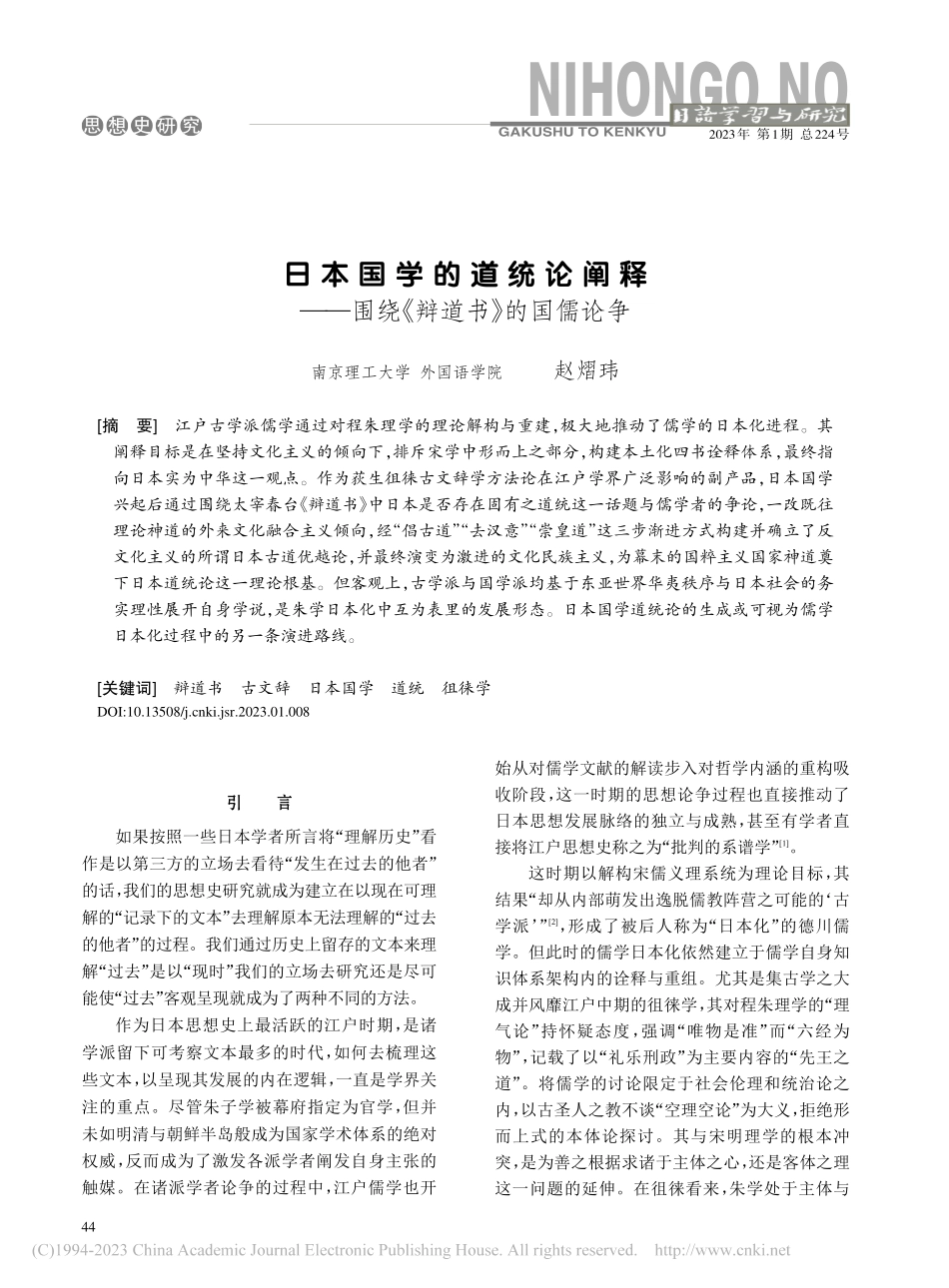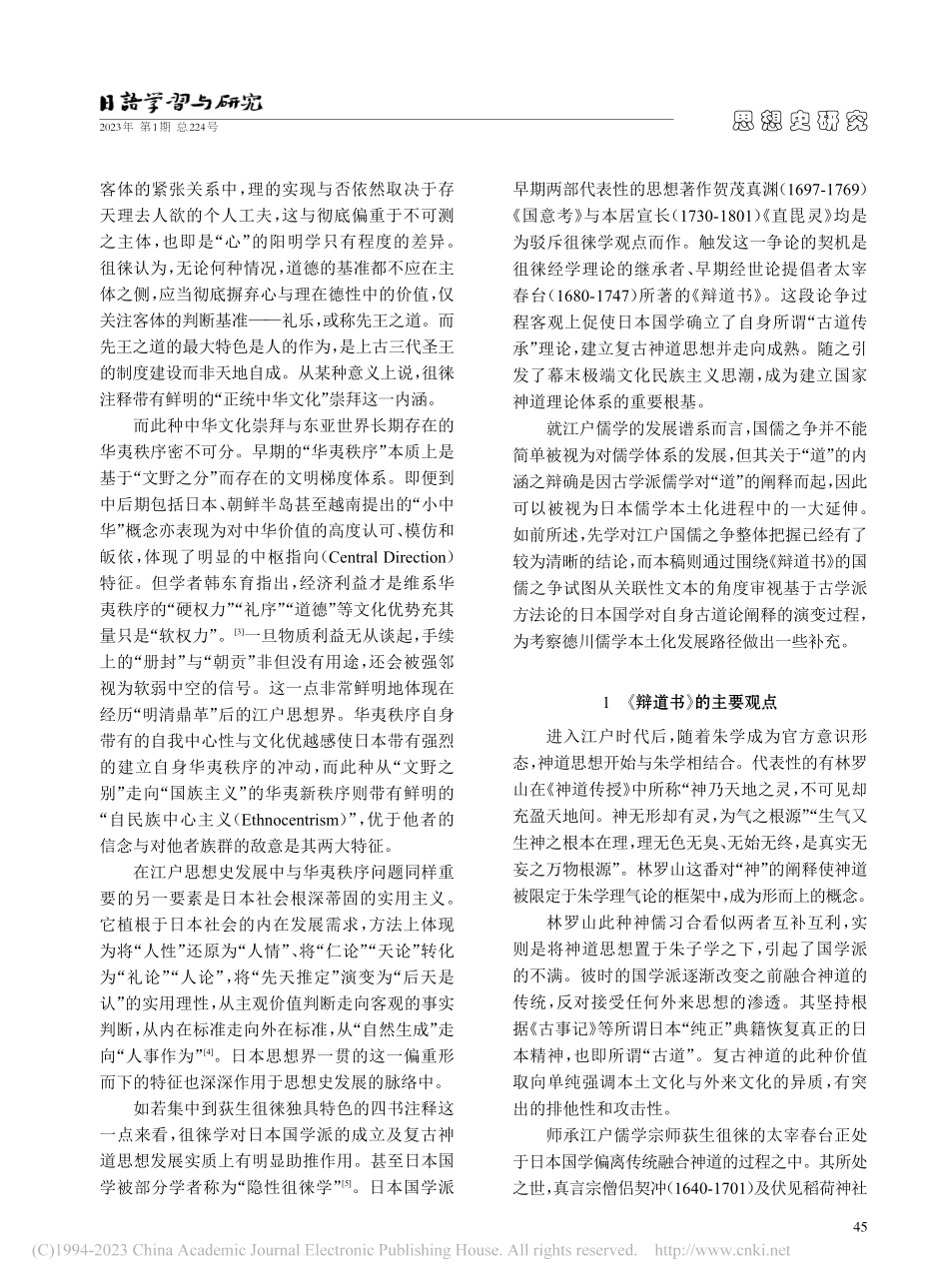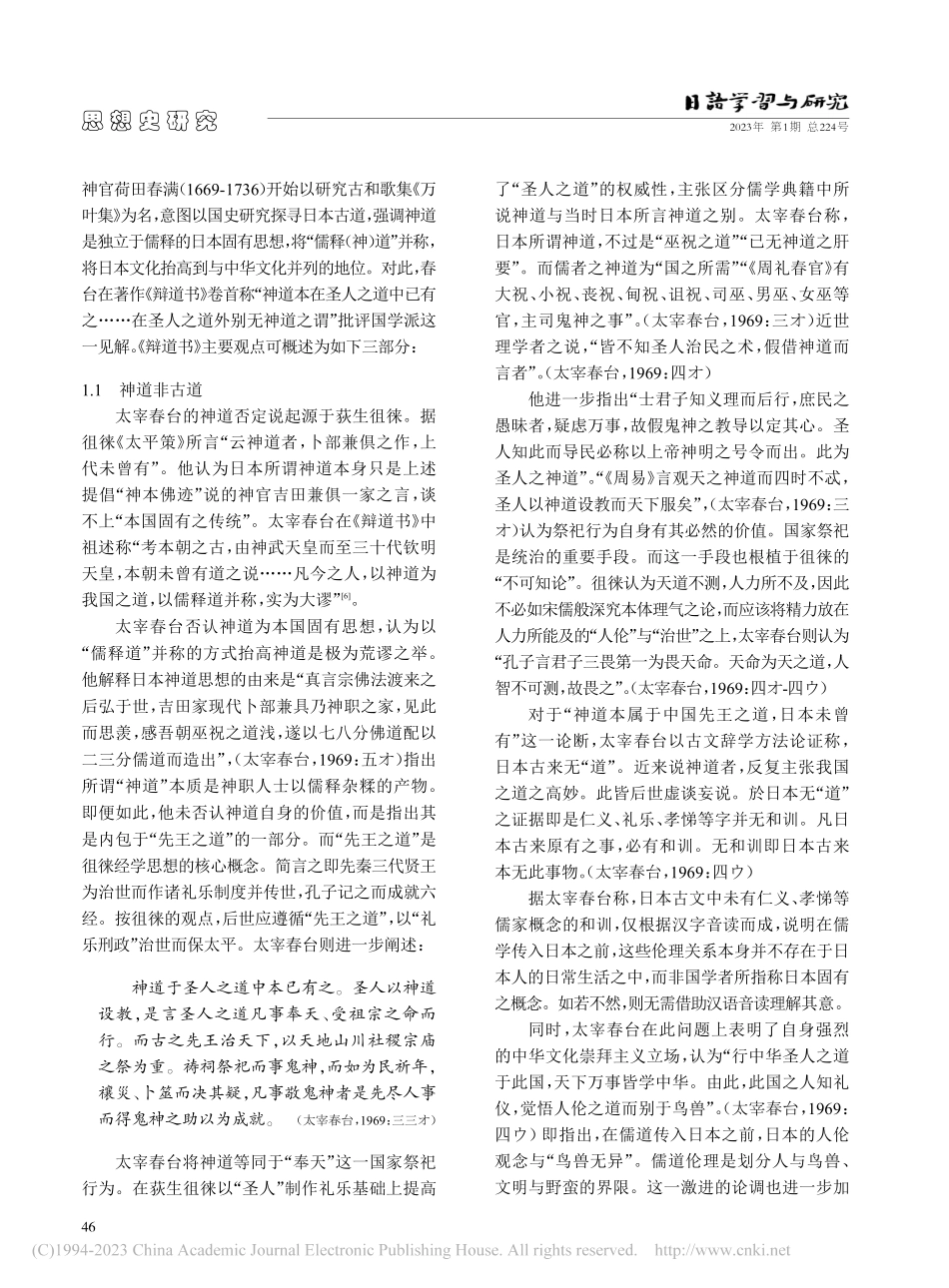引言如果按照一些日本学者所言将“理解历史”看作是以第三方的立场去看待“发生在过去的他者”的话,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就成为建立在以现在可理解的“记录下的文本”去理解原本无法理解的“过去的他者”的过程。我们通过历史上留存的文本来理解“过去”是以“现时”我们的立场去研究还是尽可能使“过去”客观呈现就成为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作为日本思想史上最活跃的江户时期,是诸学派留下可考察文本最多的时代,如何去梳理这些文本,以呈现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尽管朱子学被幕府指定为官学,但并未如明清与朝鲜半岛般成为国家学术体系的绝对权威,反而成为了激发各派学者阐发自身主张的触媒。在诸派学者论争的过程中,江户儒学也开始从对儒学文献的解读步入对哲学内涵的重构吸收阶段,这一时期的思想论争过程也直接推动了日本思想发展脉络的独立与成熟,甚至有学者直接将江户思想史称之为“批判的系谱学”[1]。这时期以解构宋儒义理系统为理论目标,其结果“却从内部萌发出逸脱儒教阵营之可能的‘古学派’”[2],形成了被后人称为“日本化”的德川儒学。但此时的儒学日本化依然建立于儒学自身知识体系架构内的诠释与重组。尤其是集古学之大成并风靡江户中期的徂徕学,其对程朱理学的“理气论”持怀疑态度,强调“唯物是准”而“六经为物”,记载了以“礼乐刑政”为主要内容的“先王之道”。将儒学的讨论限定于社会伦理和统治论之内,以古圣人之教不谈“空理空论”为大义,拒绝形而上式的本体论探讨。其与宋明理学的根本冲突,是为善之根据求诸于主体之心,还是客体之理这一问题的延伸。在徂徕看来,朱学处于主体与日本国学的道统论阐释——围绕《辩道书》的国儒论争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赵熠玮[摘要]江户古学派儒学通过对程朱理学的理论解构与重建,极大地推动了儒学的日本化进程。其阐释目标是在坚持文化主义的倾向下,排斥宋学中形而上之部分,构建本土化四书诠释体系,最终指向日本实为中华这一观点。作为荻生徂徕古文辞学方法论在江户学界广泛影响的副产品,日本国学兴起后通过围绕太宰春台《辩道书》中日本是否存在固有之道统这一话题与儒学者的争论,一改既往理论神道的外来文化融合主义倾向,经“倡古道”“去汉意”“崇皇道”这三步渐进方式构建并确立了反文化主义的所谓日本古道优越论,并最终演变为激进的文化民族主义,为幕末的国粹主义国家神道奠下日本道统论这一理论根基。但客观上,古学派与国学派均基于东亚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