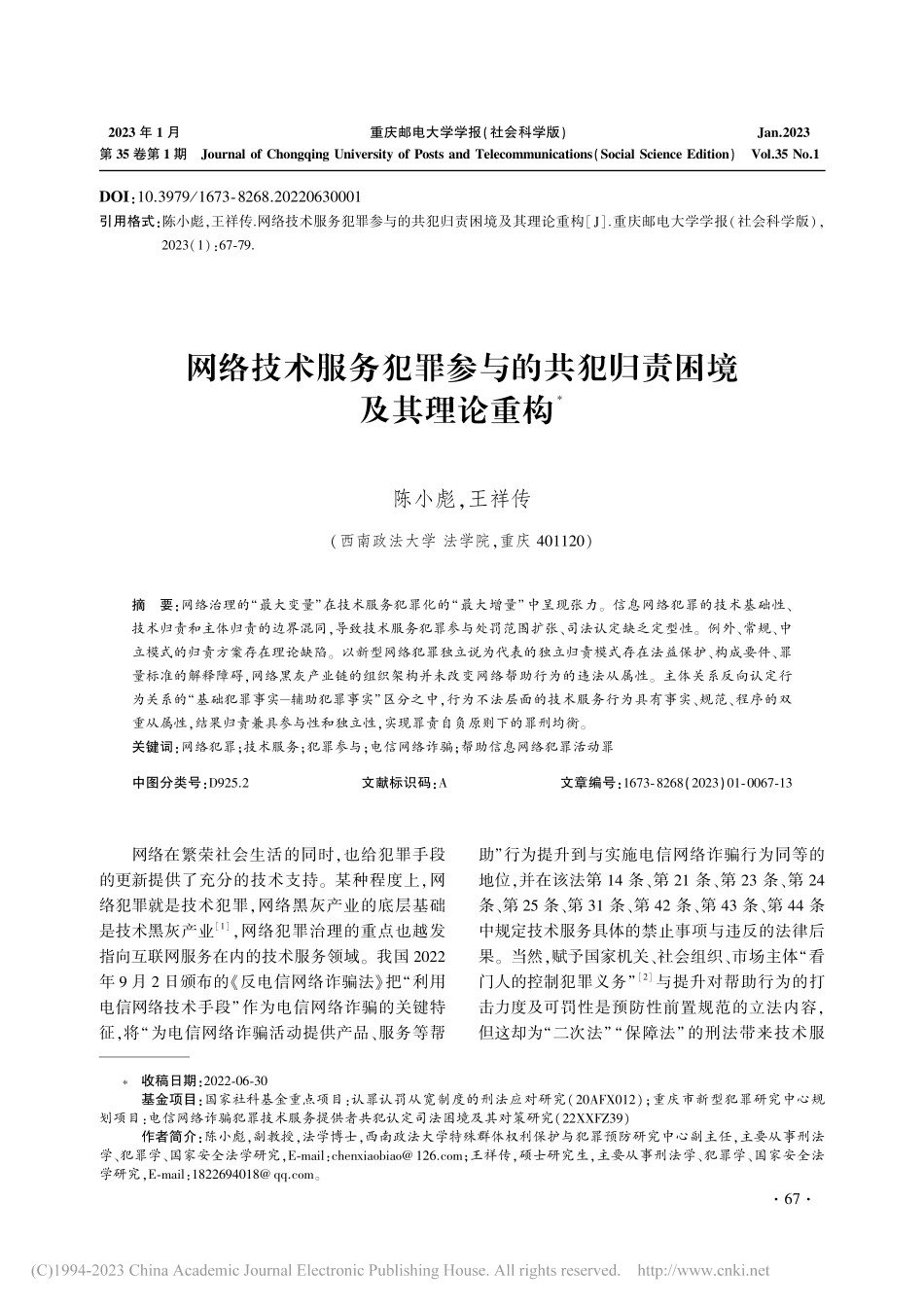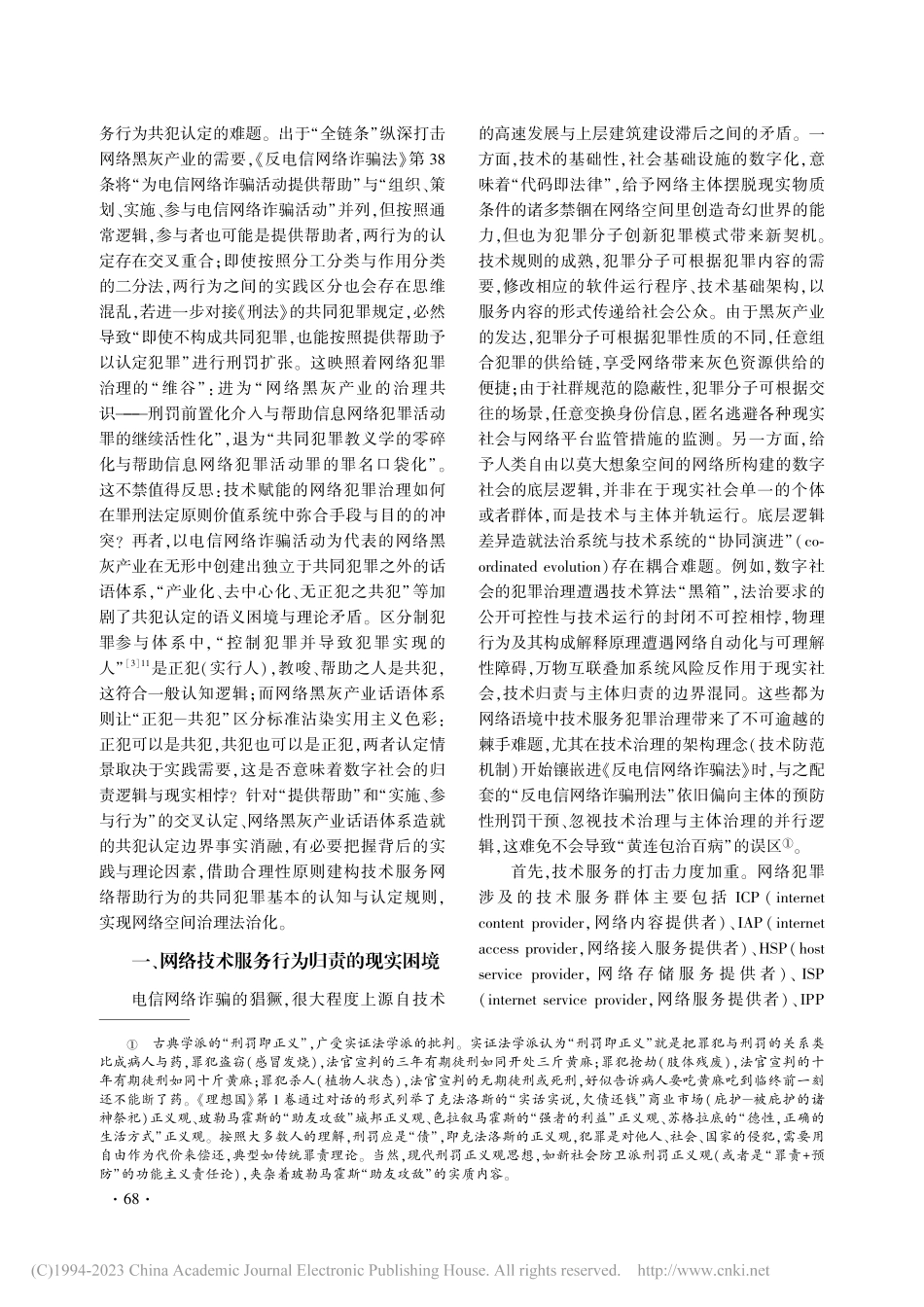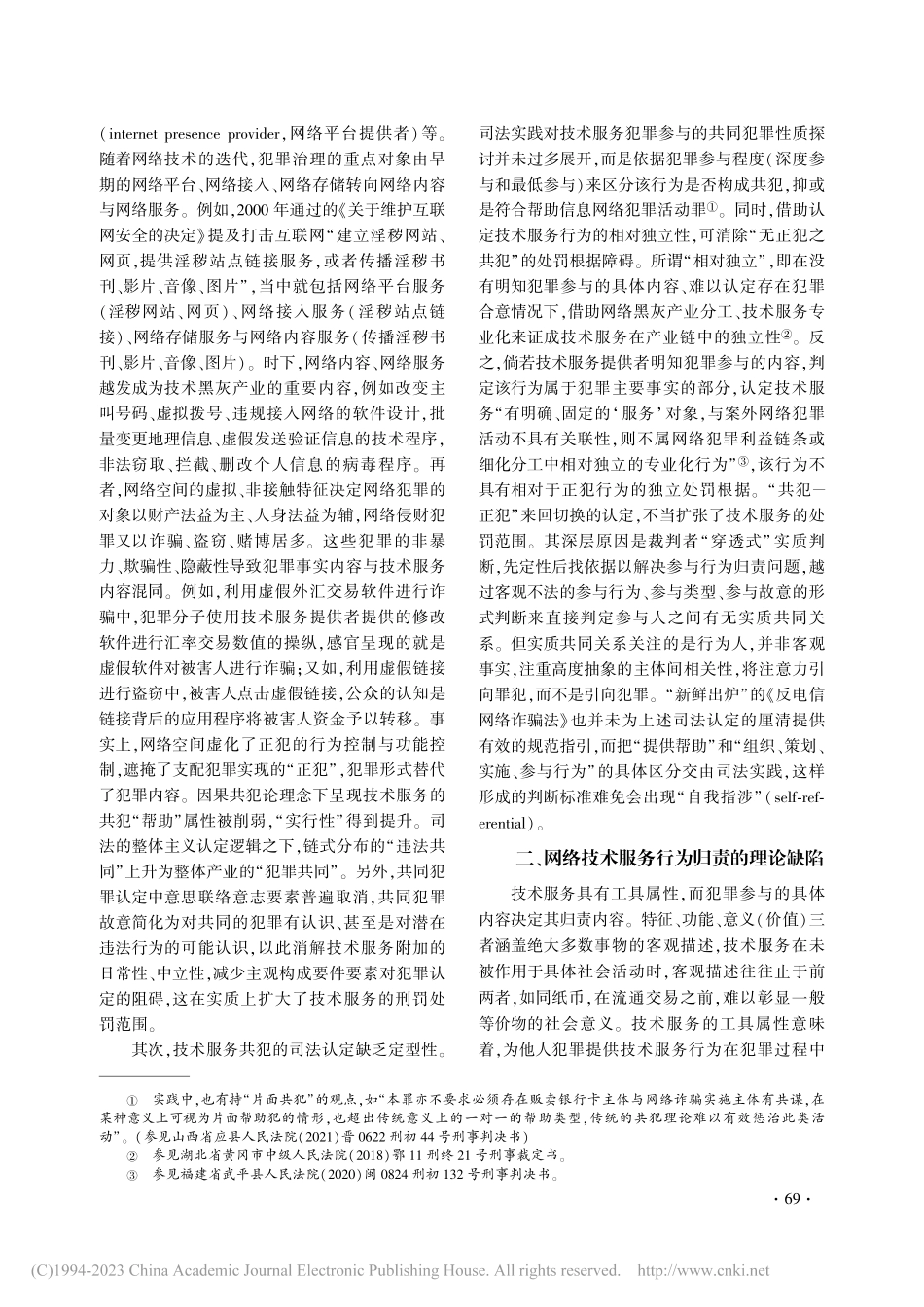2023年1月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an.2023第35卷第1期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ofPostsandTelecommunications(SocialScienceEdition)Vol.35No.1DOI:10.3979/1673⁃8268.20220630001引用格式:陈小彪,王祥传.网络技术服务犯罪参与的共犯归责困境及其理论重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67⁃79.网络技术服务犯罪参与的共犯归责困境及其理论重构∗陈小彪,王祥传(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摘要:网络治理的“最大变量”在技术服务犯罪化的“最大增量”中呈现张力。信息网络犯罪的技术基础性、技术归责和主体归责的边界混同,导致技术服务犯罪参与处罚范围扩张、司法认定缺乏定型性。例外、常规、中立模式的归责方案存在理论缺陷。以新型网络犯罪独立说为代表的独立归责模式存在法益保护、构成要件、罪量标准的解释障碍,网络黑灰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并未改变网络帮助行为的违法从属性。主体关系反向认定行为关系的“基础犯罪事实辅助犯罪事实”区分之中,行为不法层面的技术服务行为具有事实、规范、程序的双重从属性,结果归责兼具参与性和独立性,实现罪责自负原则下的罪刑均衡。关键词:网络犯罪;技术服务;犯罪参与;电信网络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图分类号:D9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23)01⁃0067⁃13网络在繁荣社会生活的同时,也给犯罪手段的更新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支持。某种程度上,网络犯罪就是技术犯罪,网络黑灰产业的底层基础是技术黑灰产业[1],网络犯罪治理的重点也越发指向互联网服务在内的技术服务领域。我国2022年9月2日颁布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把“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关键特征,将“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产品、服务等帮助”行为提升到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行为同等的地位,并在该法第14条、第21条、第23条、第24条、第25条、第31条、第42条、第43条、第44条中规定技术服务具体的禁止事项与违反的法律后果。当然,赋予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看门人的控制犯罪义务”[2]与提升对帮助行为的打击力度及可罚性是预防性前置规范的立法内容,但这却为“二次法”“保障法”的刑法带来技术服·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