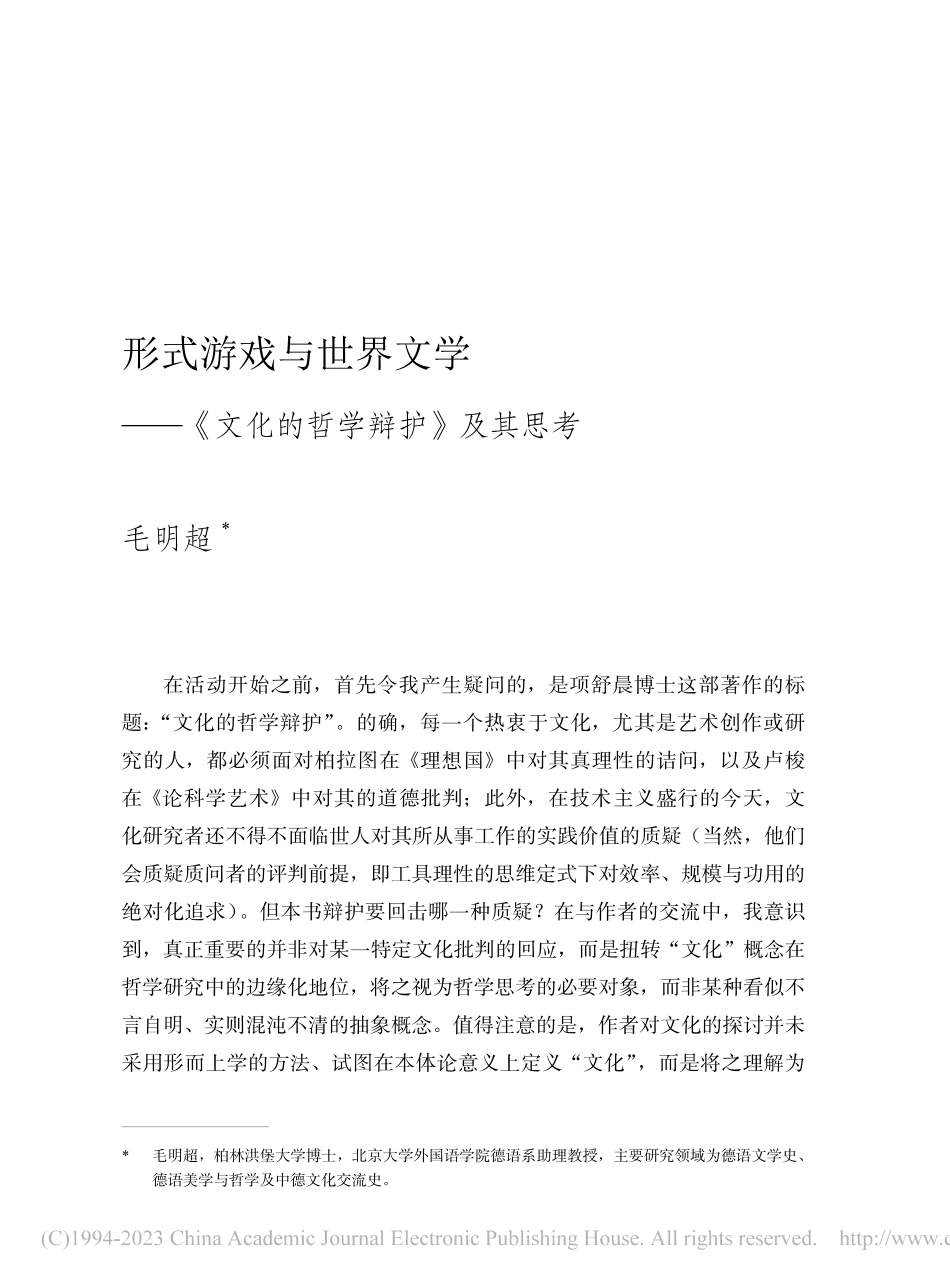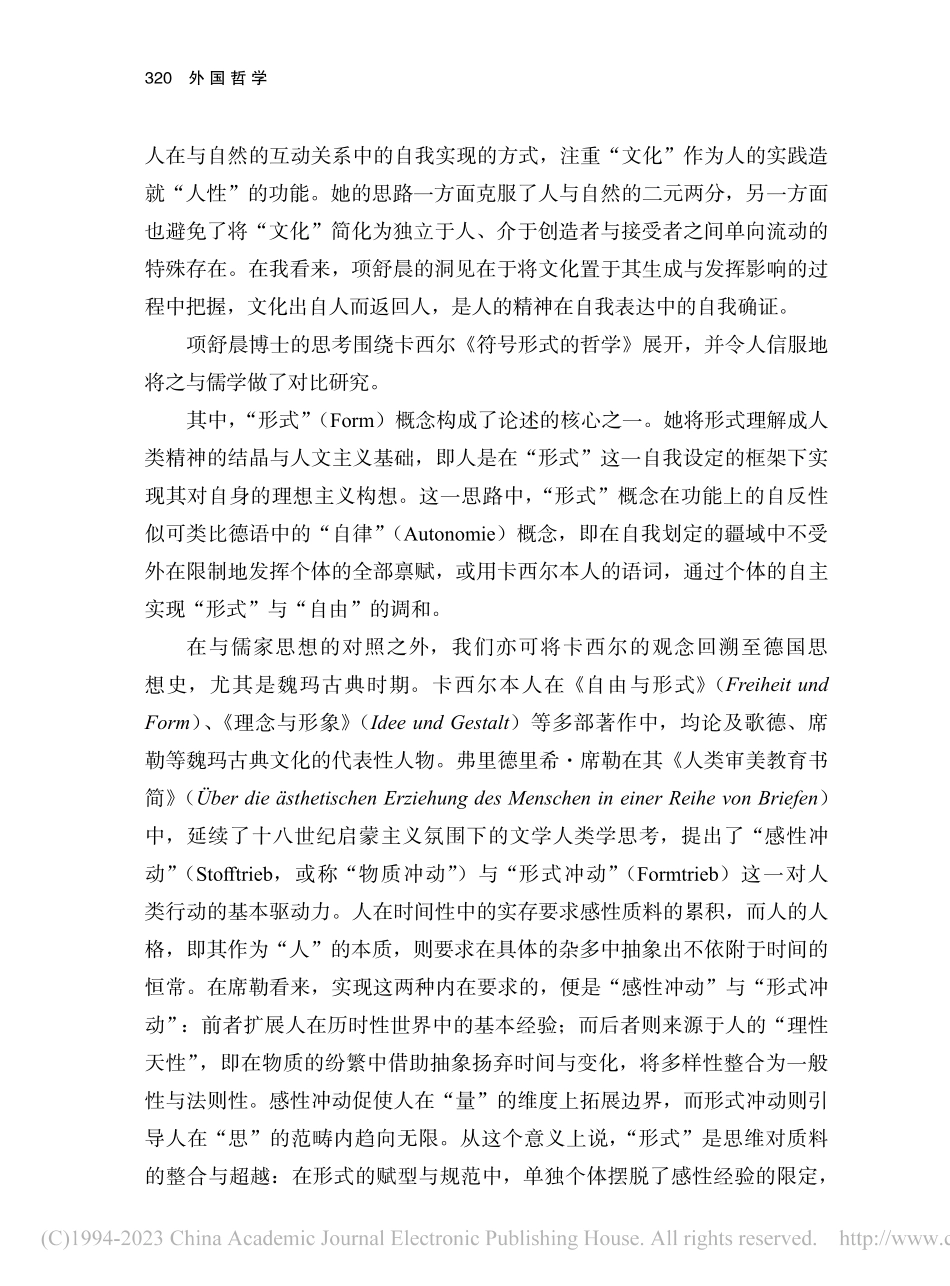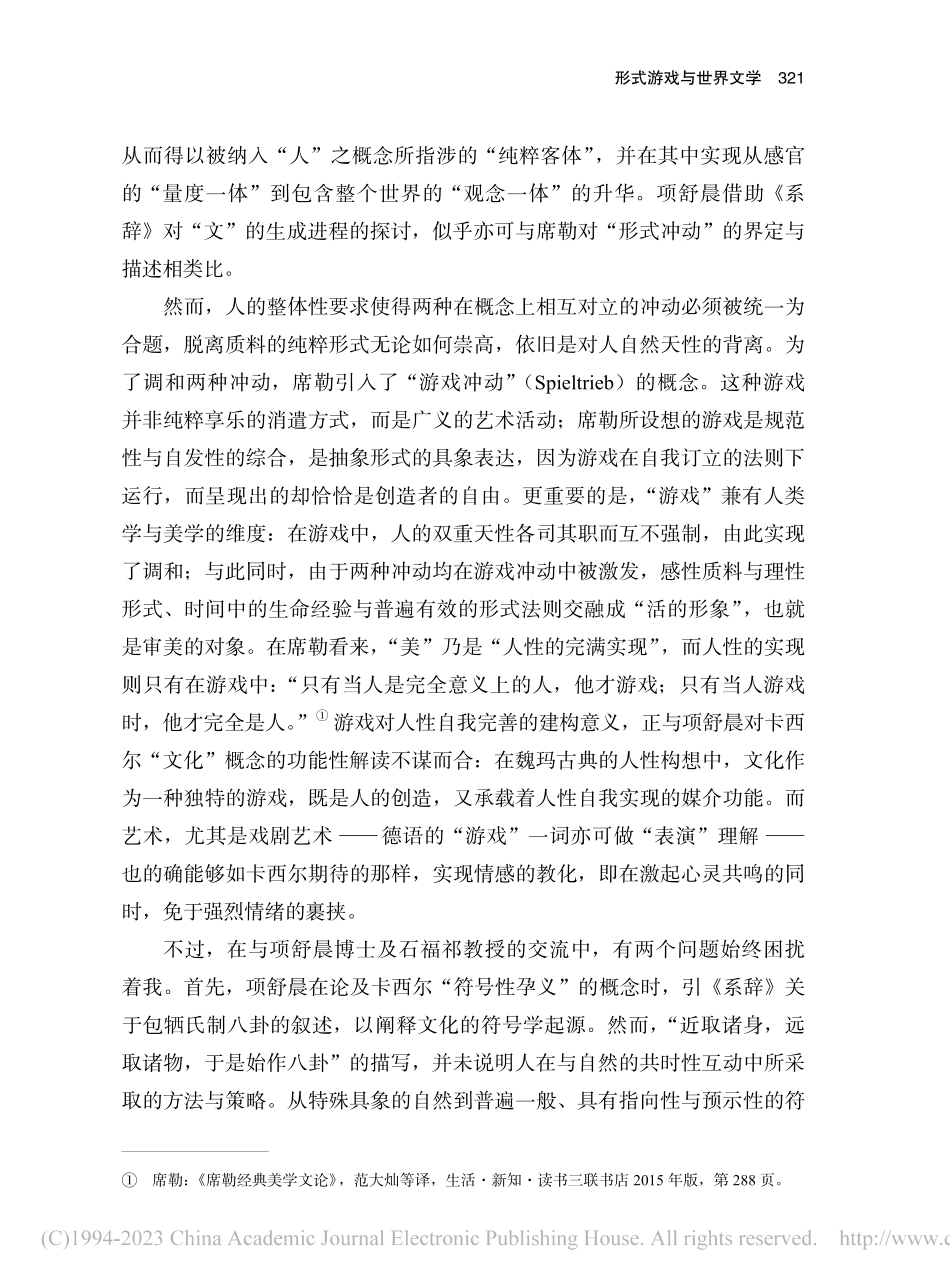形式游戏与世界文学—《文化的哲学辩护》及其思考毛明超*在活动开始之前,首先令我产生疑问的,是项舒晨博士这部著作的标题:“文化的哲学辩护”。的确,每一个热衷于文化,尤其是艺术创作或研究的人,都必须面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其真理性的诘问,以及卢梭在《论科学艺术》中对其的道德批判;此外,在技术主义盛行的今天,文化研究者还不得不面临世人对其所从事工作的实践价值的质疑(当然,他们会质疑质问者的评判前提,即工具理性的思维定式下对效率、规模与功用的绝对化追求)。但本书辩护要回击哪一种质疑?在与作者的交流中,我意识到,真正重要的并非对某一特定文化批判的回应,而是扭转“文化”概念在哲学研究中的边缘化地位,将之视为哲学思考的必要对象,而非某种看似不言自明、实则混沌不清的抽象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文化的探讨并未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试图在本体论意义上定义“文化”,而是将之理解为*毛明超,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德语文学史、德语美学与哲学及中德文化交流史。320外国哲学人在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中的自我实现的方式,注重“文化”作为人的实践造就“人性”的功能。她的思路一方面克服了人与自然的二元两分,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将“文化”简化为独立于人、介于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单向流动的特殊存在。在我看来,项舒晨的洞见在于将文化置于其生成与发挥影响的过程中把握,文化出自人而返回人,是人的精神在自我表达中的自我确证。项舒晨博士的思考围绕卡西尔《符号形式的哲学》展开,并令人信服地将之与儒学做了对比研究。其中,“形式”(Form)概念构成了论述的核心之一。她将形式理解成人类精神的结晶与人文主义基础,即人是在“形式”这一自我设定的框架下实现其对自身的理想主义构想。这一思路中,“形式”概念在功能上的自反性似可类比德语中的“自律”(Autonomie)概念,即在自我划定的疆域中不受外在限制地发挥个体的全部禀赋,或用卡西尔本人的语词,通过个体的自主实现“形式”与“自由”的调和。在与儒家思想的对照之外,我们亦可将卡西尔的观念回溯至德国思想史,尤其是魏玛古典时期。卡西尔本人在《自由与形式》(FreiheitundForm)、《理念与形象》(IdeeundGestalt)等多部著作中,均论及歌德、席勒等魏玛古典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弗里德里希·席勒在其《人类审美教育书简》(ÜberdieästhetischenErziehungdesMenschenineinerReihevonBrie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