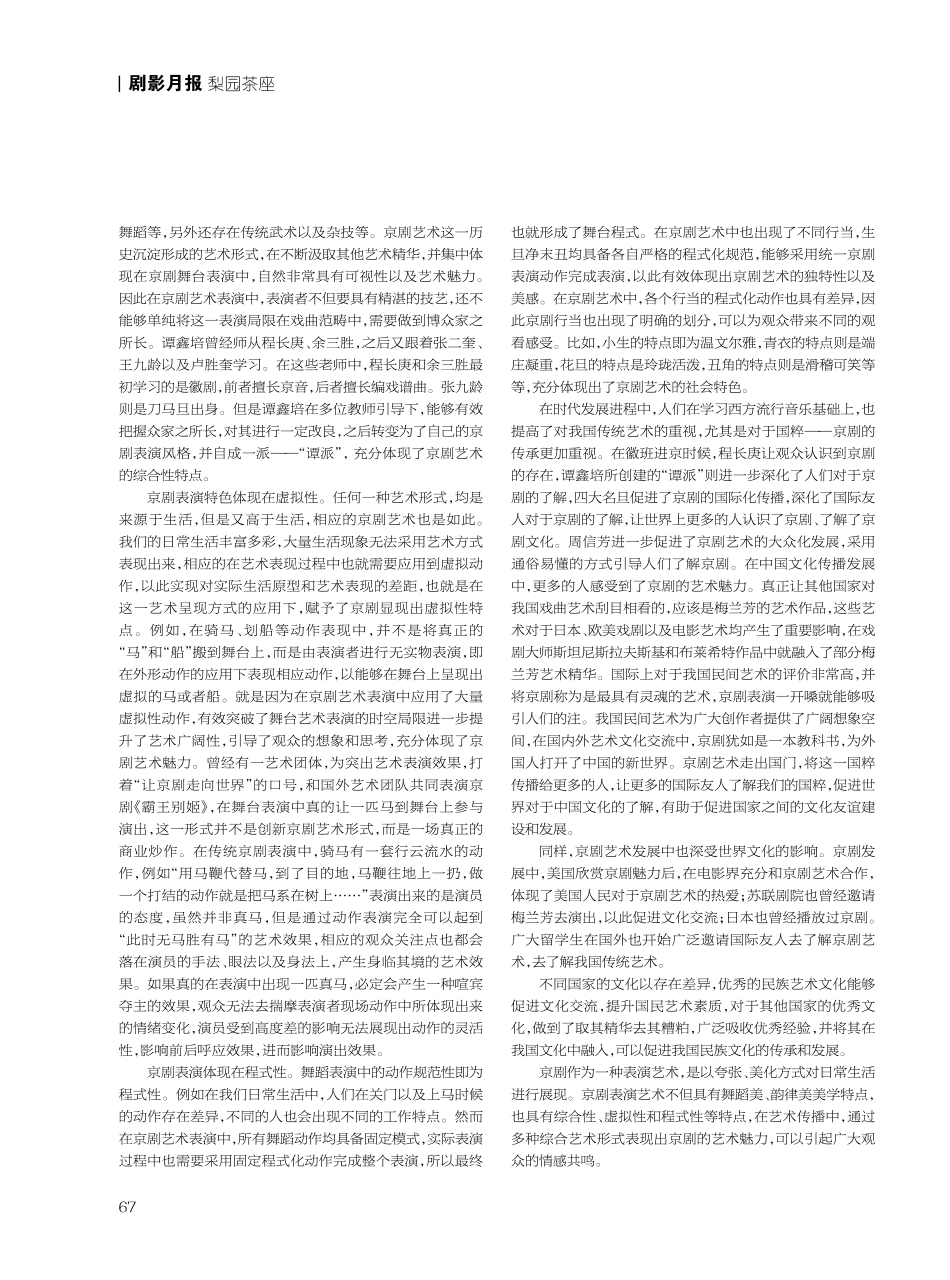区宽,高音区幽窄,若瞬间升至八度音,气息释放难以聚集。我经过多次尝试,把起板的四、七字换气,改成一、四、七字的气息转接。这一叹三泣,加长了起腔的铺垫,气息的释放从容,恰浓郁了唱腔的气氛。在后半段的数板里,我坚持住中音叠字句的运气,出字包句均在板点子的起槌时汲气,轻放轻收,唱得极其放松和饱满。只有找准自我的声腔定位,演唱才会个性起来,才会有独特的感染力。四、突破程式化腔为境淮剧唱腔的呈现是以板腔体为主、曲牌体为辅的综合曲体结构。曲调有淮调、拉调、自由调三大主要调式。淮调,高亢激越,诉说性强,大多用于叙事;拉调,委婉细腻,线条清新,适用于抒情性的场景;自由调,旋律流畅,可塑性大,具有综合的表现功能。这些丰富的曲调为淮剧的唱腔表现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已成熟的曲牌也为演员提供了多姿多彩的表演“花头”,往往一个曲调由不同演员演唱均有不一样的效果,日久天长,渐渐地出现了“独家特色”的流派。关于唱腔的表达,一般有两个不同的理解。一是唯唱腔而展开演唱,这在过去旧艺人中比较讨彩,演唱声音大,演唱者往往陶醉在悠然自得之中,幕表形式的演出时,更是掺杂着故作炫技的即兴表演。二是情感化,化腔于戏,这便是善于把唱腔带入故事的叙述之中,唱腔是被剧情、人物感情包裹着的,达到一定境界时,唱腔所有的词曲亦成意念,出神入化。我以为“唱情”比“唱调子”更有内涵,唱情是把词曲活态化的二度创作,是真正的唱腔风格。根据理解的不同,表现程度有差异而各有千秋。把唱腔转化成戏的情绪,与剧情、人物紧紧黏合,成就特别的声腔意境,是我在40年的表演实践中认真探索的方向。我是淮剧名家陈德林先生的嫡传弟子,拜师是为了更好地把淮剧艺术发扬光大。他的“陈派生腔”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创造性地将淮剧“生腔”“旦腔”并轨,打破了一贯的淮剧生腔本嗓发音方式,拓展了生腔的表现力,这种唱法在淮剧海派(上海)生腔中运用尤广。我曾在传统戏《团圆之后》里饰演施佾生一角。剧中有个高潮唱段,表现十八年后,施佾生才识得生父,却又因自己是个私生子,为状元名节、富贵荣华而毒杀生父,充满了悔恨交加的复杂情绪。这里的原唱是陈德林先生,开腔十分地热烈、激越。我根据自身的嗓音特点,结合对台词的理解,弱化气息在演唱过程中的程式,充分地化腔为境,以境入腔。在过门的铺垫之后,瞬间把唱腔带入戏情:“一声叫爹喉哽咽,十八年来头一回。只道生父永难见,今日亲父来把儿陪”,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