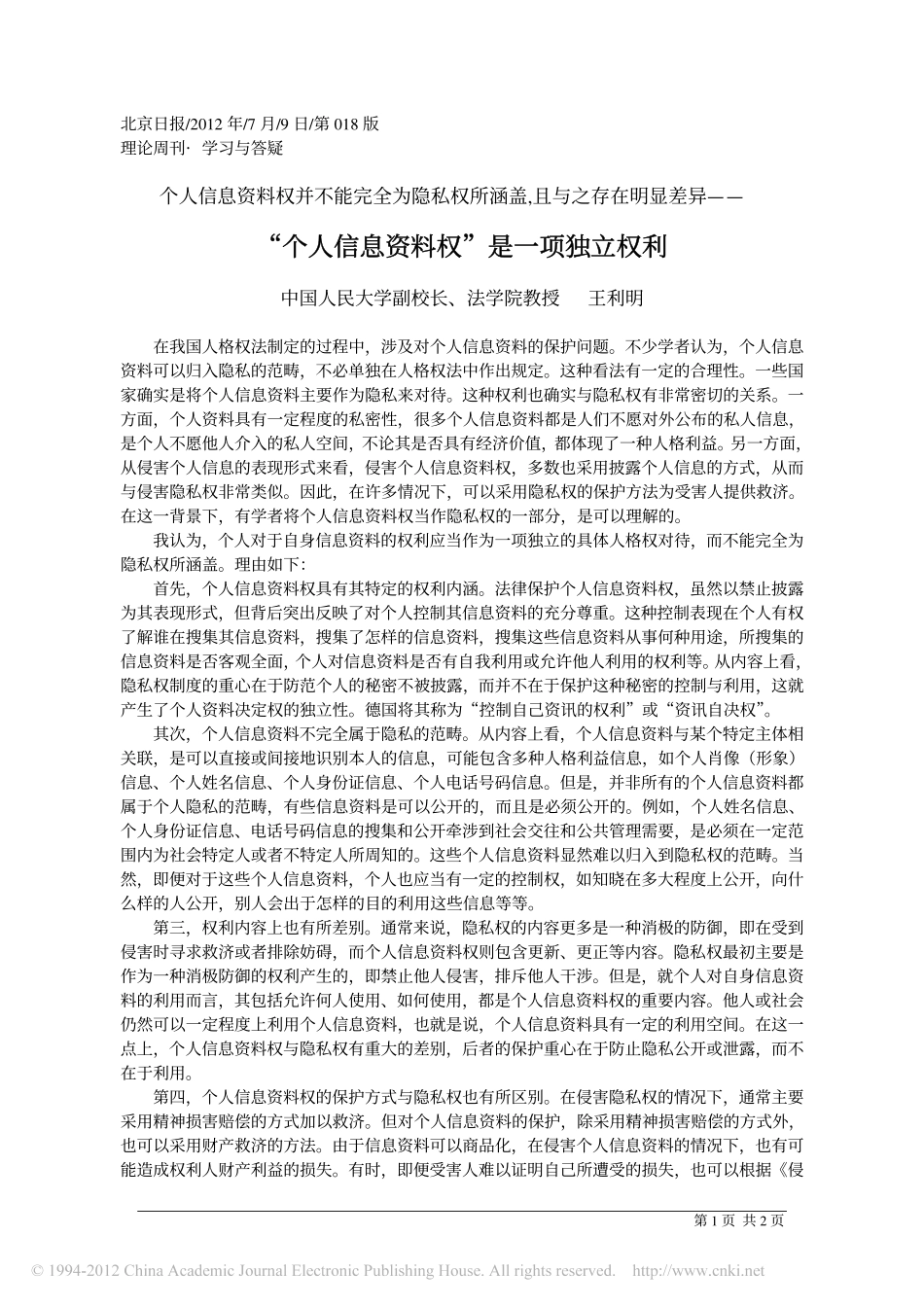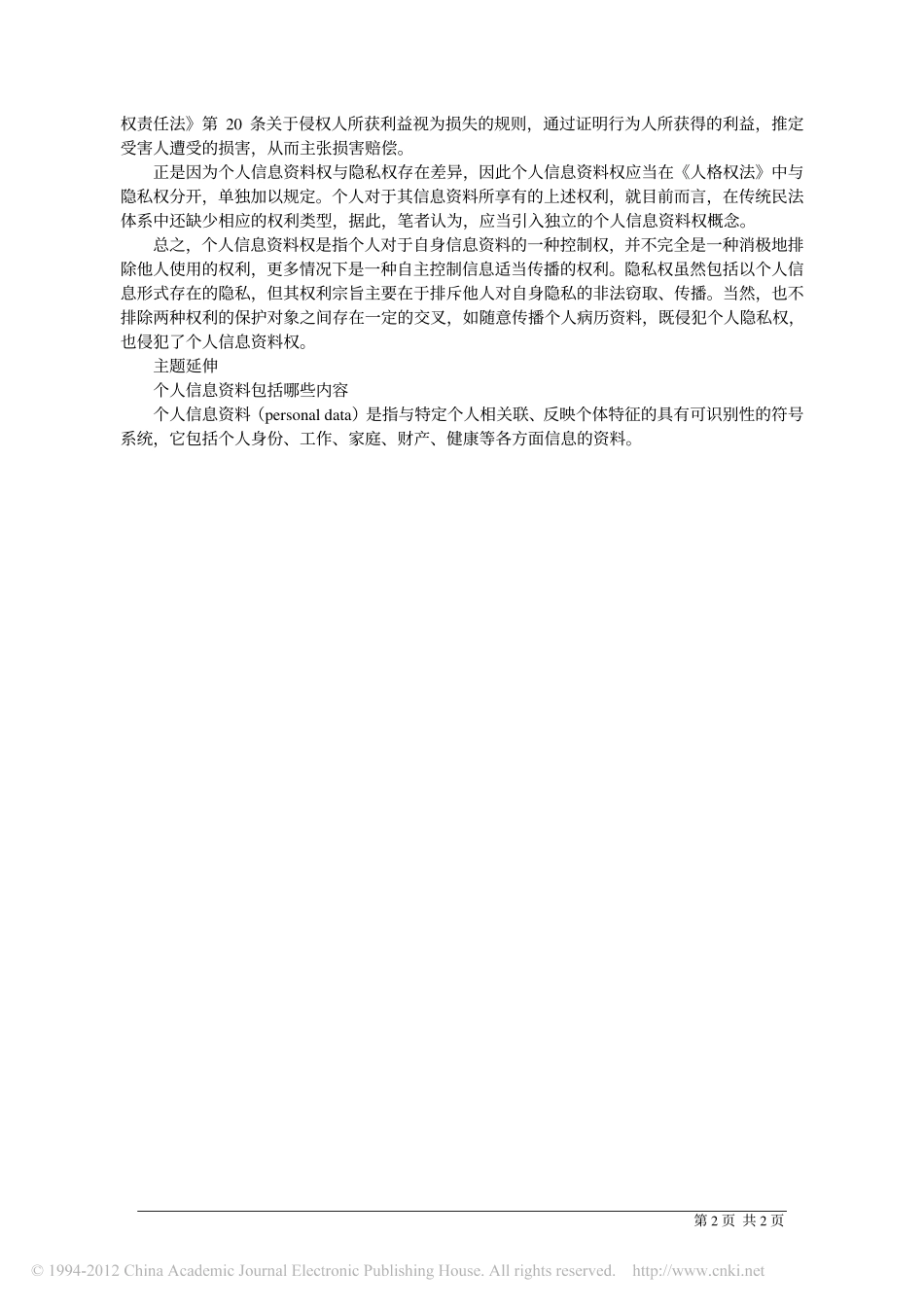第1页共2页北京日报/2012年/7月/9日/第018版理论周刊·学习与答疑个人信息资料权并不能完全为隐私权所涵盖,且与之存在明显差异——“个人信息资料权”是一项独立权利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法学院教授王利明在我国人格权法制定的过程中,涉及对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个人信息资料可以归入隐私的范畴,不必单独在人格权法中作出规定。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些国家确实是将个人信息资料主要作为隐私来对待。这种权利也确实与隐私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个人资料具有一定程度的私密性,很多个人信息资料都是人们不愿对外公布的私人信息,是个人不愿他人介入的私人空间,不论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都体现了一种人格利益。另一方面,从侵害个人信息的表现形式来看,侵害个人信息资料权,多数也采用披露个人信息的方式,从而与侵害隐私权非常类似。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可以采用隐私权的保护方法为受害人提供救济。在这一背景下,有学者将个人信息资料权当作隐私权的一部分,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个人对于自身信息资料的权利应当作为一项独立的具体人格权对待,而不能完全为隐私权所涵盖。理由如下:首先,个人信息资料权具有其特定的权利内涵。法律保护个人信息资料权,虽然以禁止披露为其表现形式,但背后突出反映了对个人控制其信息资料的充分尊重。这种控制表现在个人有权了解谁在搜集其信息资料,搜集了怎样的信息资料,搜集这些信息资料从事何种用途,所搜集的信息资料是否客观全面,个人对信息资料是否有自我利用或允许他人利用的权利等。从内容上看,隐私权制度的重心在于防范个人的秘密不被披露,而并不在于保护这种秘密的控制与利用,这就产生了个人资料决定权的独立性。德国将其称为“控制自己资讯的权利”或“资讯自决权”。其次,个人信息资料不完全属于隐私的范畴。从内容上看,个人信息资料与某个特定主体相关联,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识别本人的信息,可能包含多种人格利益信息,如个人肖像(形象)信息、个人姓名信息、个人身份证信息、个人电话号码信息。但是,并非所有的个人信息资料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有些信息资料是可以公开的,而且是必须公开的。例如,个人姓名信息、个人身份证信息、电话号码信息的搜集和公开牵涉到社会交往和公共管理需要,是必须在一定范围内为社会特定人或者不特定人所周知的。这些个人信息资料显然难以归入到隐私权的范畴。当然,即便对于这些个人信息资料,个人也应当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