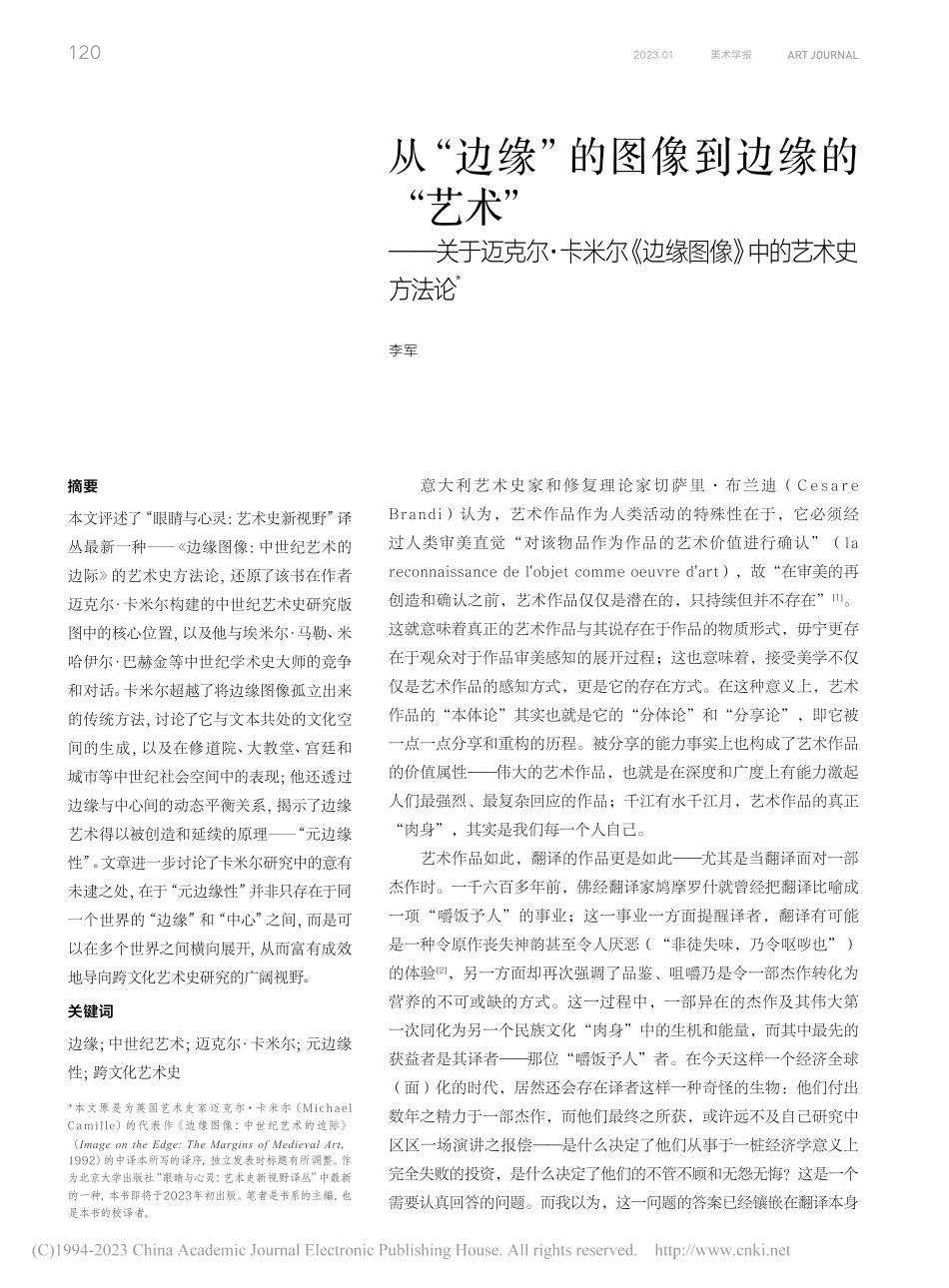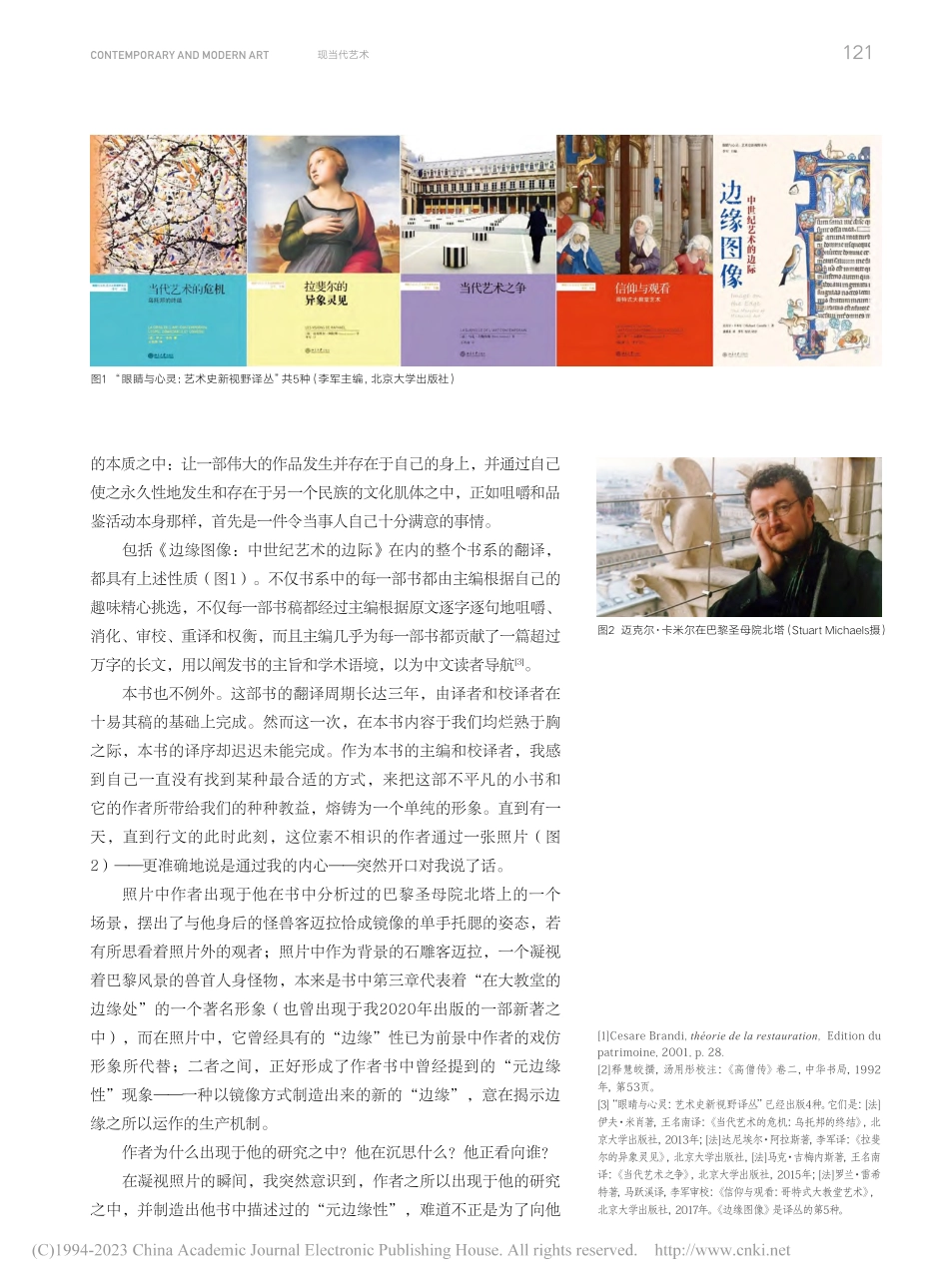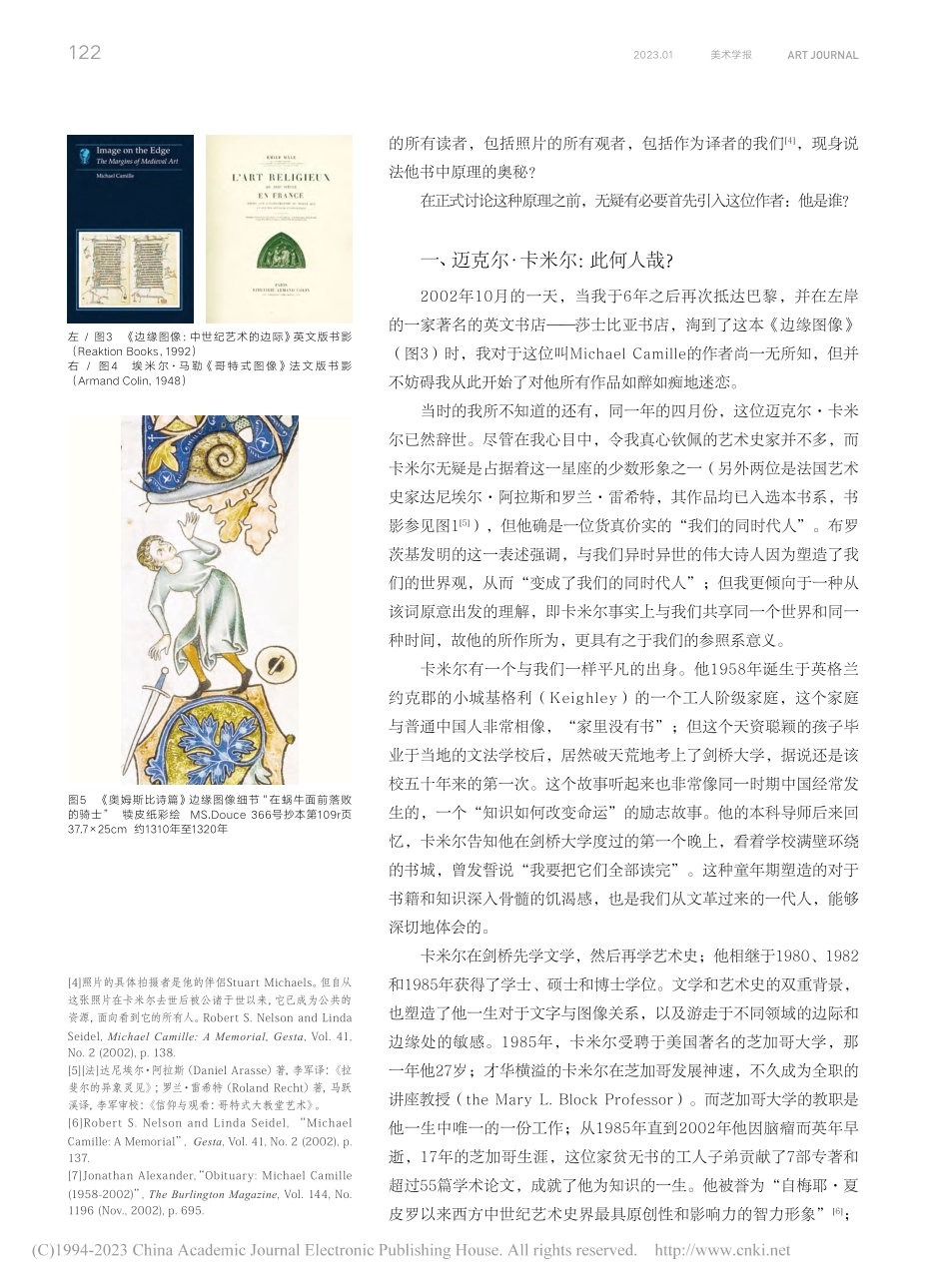120美术学报ARTJOURNAL2023.01从“边缘”的图像到边缘的“艺术”——关于迈克尔·卡米尔《边缘图像》中的艺术史方法论*李军摘要本文评述了“眼睛与心灵:艺术史新视野”译丛最新一种——《边缘图像:中世纪艺术的边际》的艺术史方法论,还原了该书在作者迈克尔·卡米尔构建的中世纪艺术史研究版图中的核心位置,以及他与埃米尔·马勒、米哈伊尔·巴赫金等中世纪学术史大师的竞争和对话。卡米尔超越了将边缘图像孤立出来的传统方法,讨论了它与文本共处的文化空间的生成,以及在修道院、大教堂、宫廷和城市等中世纪社会空间中的表现;他还透过边缘与中心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揭示了边缘艺术得以被创造和延续的原理——“元边缘性”。文章进一步讨论了卡米尔研究中的意有未逮之处,在于“元边缘性”并非只存在于同一个世界的“边缘”和“中心”之间,而是可以在多个世界之间横向展开,从而富有成效地导向跨文化艺术史研究的广阔视野。关键词边缘;中世纪艺术;迈克尔·卡米尔;元边缘性;跨文化艺术史意大利艺术史家和修复理论家切萨里·布兰迪(CesareBrandi)认为,艺术作品作为人类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必须经过人类审美直觉“对该物品作为作品的艺术价值进行确认”(lareconnaissancedel'objetcommeoeuvred'art),故“在审美的再创造和确认之前,艺术作品仅仅是潜在的,只持续但并不存在”[1]。这就意味着真正的艺术作品与其说存在于作品的物质形式,毋宁更存在于观众对于作品审美感知的展开过程;这也意味着,接受美学不仅仅是艺术作品的感知方式,更是它的存在方式。在这种意义上,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其实也就是它的“分体论”和“分享论”,即它被一点一点分享和重构的历程。被分享的能力事实上也构成了艺术作品的价值属性——伟大的艺术作品,也就是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能力激起人们最强烈、最复杂回应的作品;千江有水千江月,艺术作品的真正“肉身”,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艺术作品如此,翻译的作品更是如此——尤其是当翻译面对一部杰作时。一千六百多年前,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就曾经把翻译比喻成一项“嚼饭予人”的事业;这一事业一方面提醒译者,翻译有可能是一种令原作丧失神韵甚至令人厌恶(“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的体验[2],另一方面却再次强调了品鉴、咀嚼乃是令一部杰作转化为营养的不可或缺的方式。这一过程中,一部异在的杰作及其伟大第一次同化为另一个民族文化“肉身”中的生机和能量,而其中最先的获益者是其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