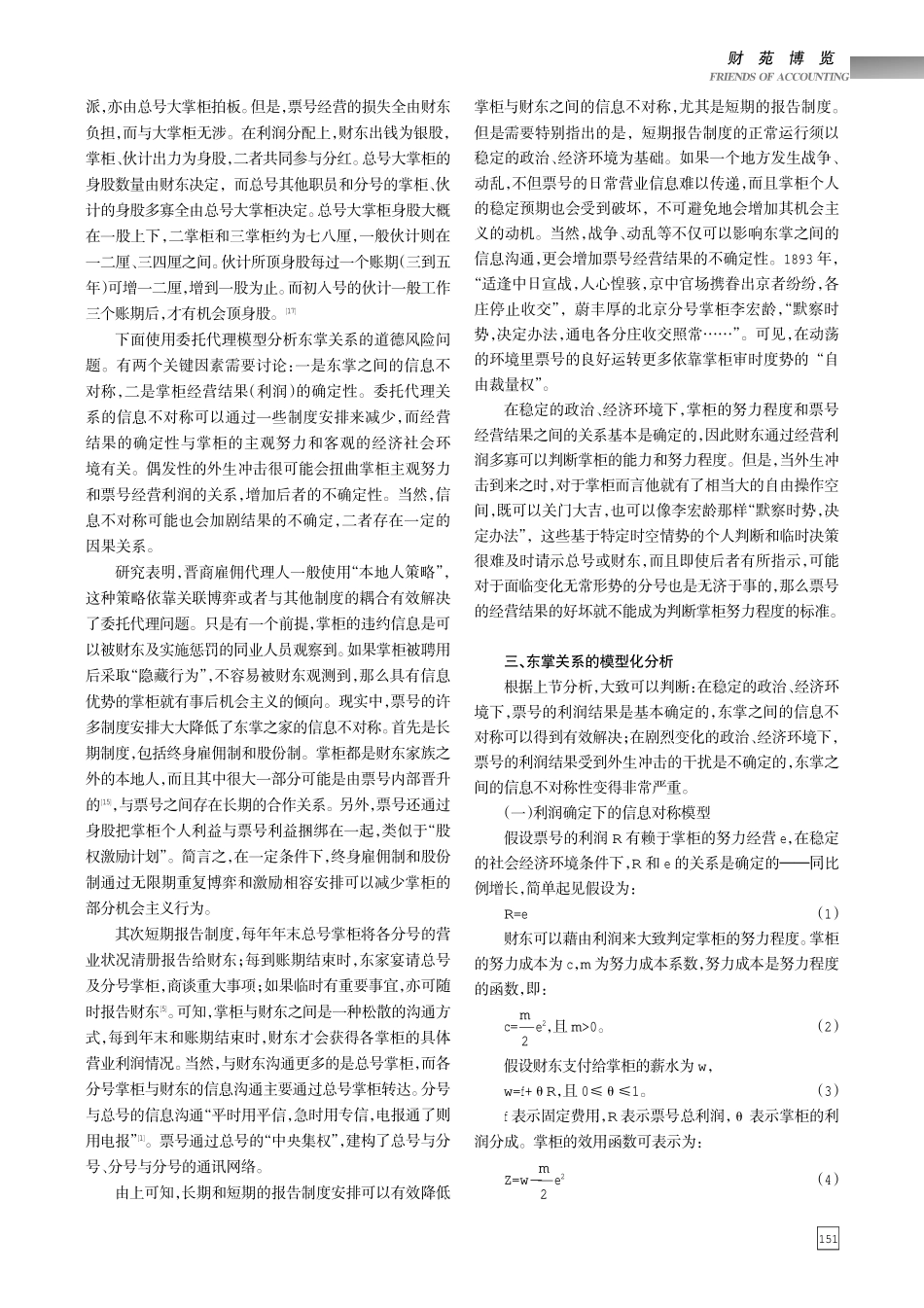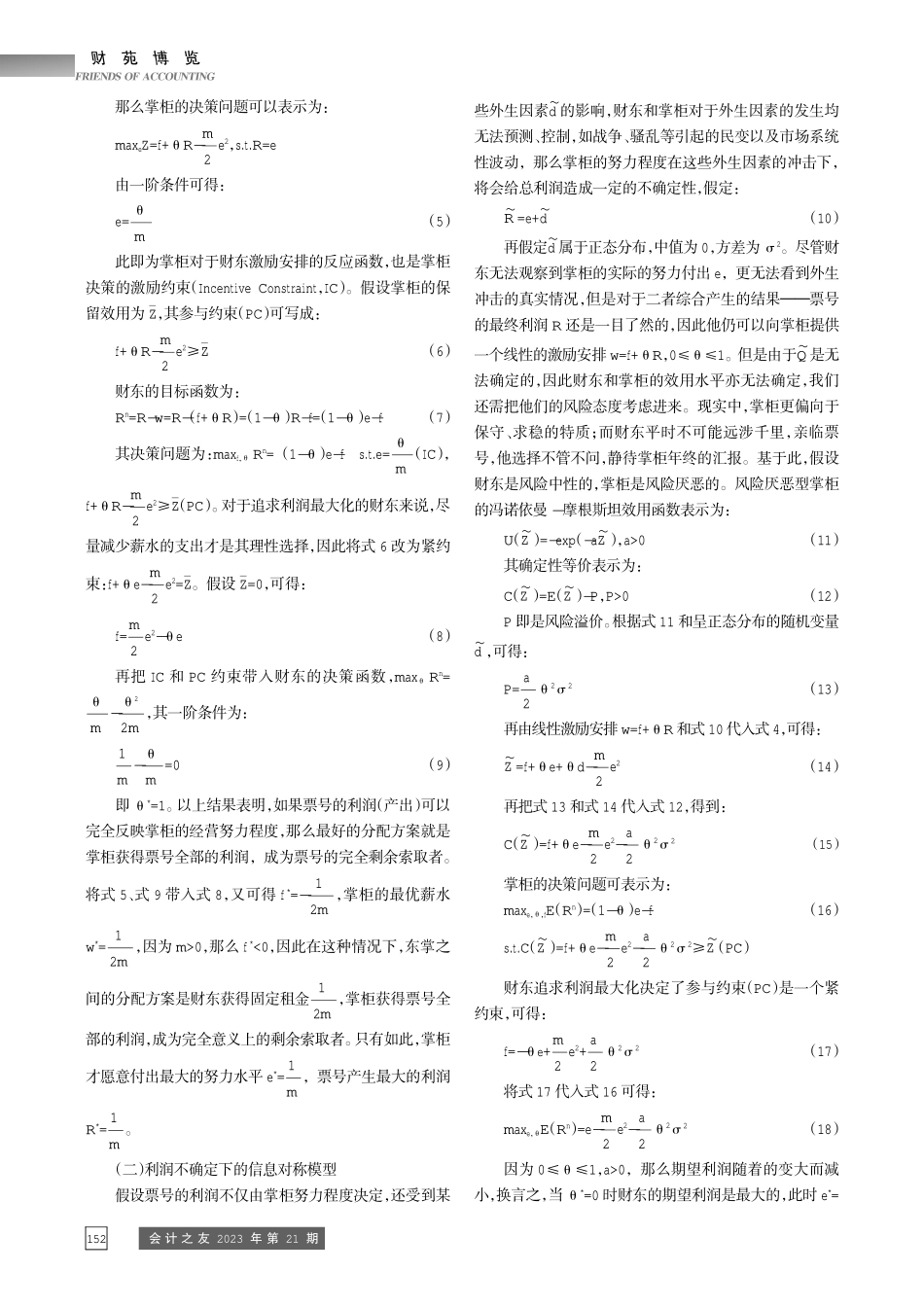会计之友2023年第21期一、引言及文献回顾晋商作为明清时代最著名的商帮,其所经营的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晋商票号管理制度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卫聚贤[1]、陈其田[2]等在民国时期就对其进行了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在孔祥毅[3]、张正明[4]、黄鉴晖[5]、史若民[6]、刘建生[7]等诸位先生的推动下,票号研究进入新时期,他们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基本廓清了晋商票号的经营管理制度,包括经理负责制、学徒制、顶身股制等。新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突破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范式,尝试使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来重新解释票号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东掌关系”。梁四宝等[8]、林柏[9]强调晋商产权制度创新对于东掌双方产生了有效的约束和激励。蔡洪滨等[10]、燕红忠[11]认为晋商内部治理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基于地缘的集体主义惩罚机制;郑文全等[12]提出票号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是靠一套高度自洽、紧密耦合的制度集合。关于票号的衰败,丰若非[13]、唐晶晶等[14]都强调“内部人控制”问题导致身股所占份额逐渐超过银股,无法对经理人产生有效约束;陈凌等[15]发现内部控制机制的缺乏导致非家族经理人的心理所有权过高,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兰日旭等[16]则更为重视票号的正副本制度在财东和经营者之间形成的双重风险放大机制。以上诸位学者使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分析、委托代理分析和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以及博弈论、公司治理等领域的研究方法,其主要问题在于大部分学者的解释框架聚焦于票号内部因素,而没有充分考虑外部环境,有的即使提到也是一笔带过。如果票号制度是大体稳定的,那么诸如“内部人控制”这种成也由之、败也由之的解释恐怕是脆弱的,它无法对票号的兴起和衰败给予逻辑一致的回答;而基于“关联博弈”的集体主义惩罚只能约束可观察到、可验证的违约行为,对于代理人的“隐藏行为”效果不大。票号财东和掌柜之间无疑是委托代理关系,他们都受到号规(正式规则)和习俗、惯例(非正式规则)的约束,双方构成事实上的契约关系。票号经营的好坏受到内外两种因素的影响,内部的因素即由于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具有信息优势的掌柜一方具有事后机会主义倾向,即“道德风险”;外部的因素即票号之外的外生冲击,如政治、经济环境的骤变等。因此,在契约理论框架内探讨信息不对称、外生冲击影响下的东掌关系,具有理论上的创新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二、东掌关系基本情况票号至迟产生于道光(1821—1850)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