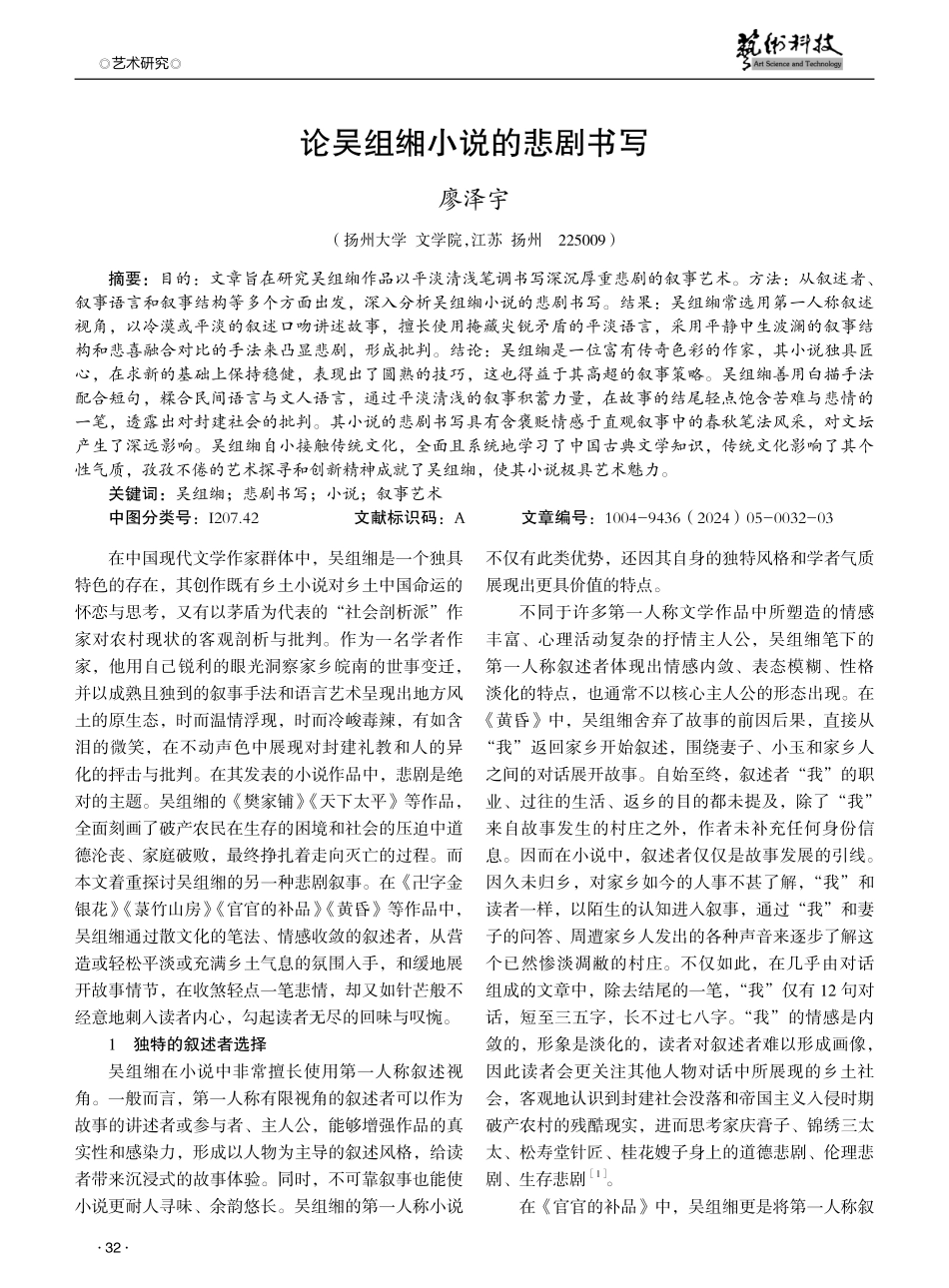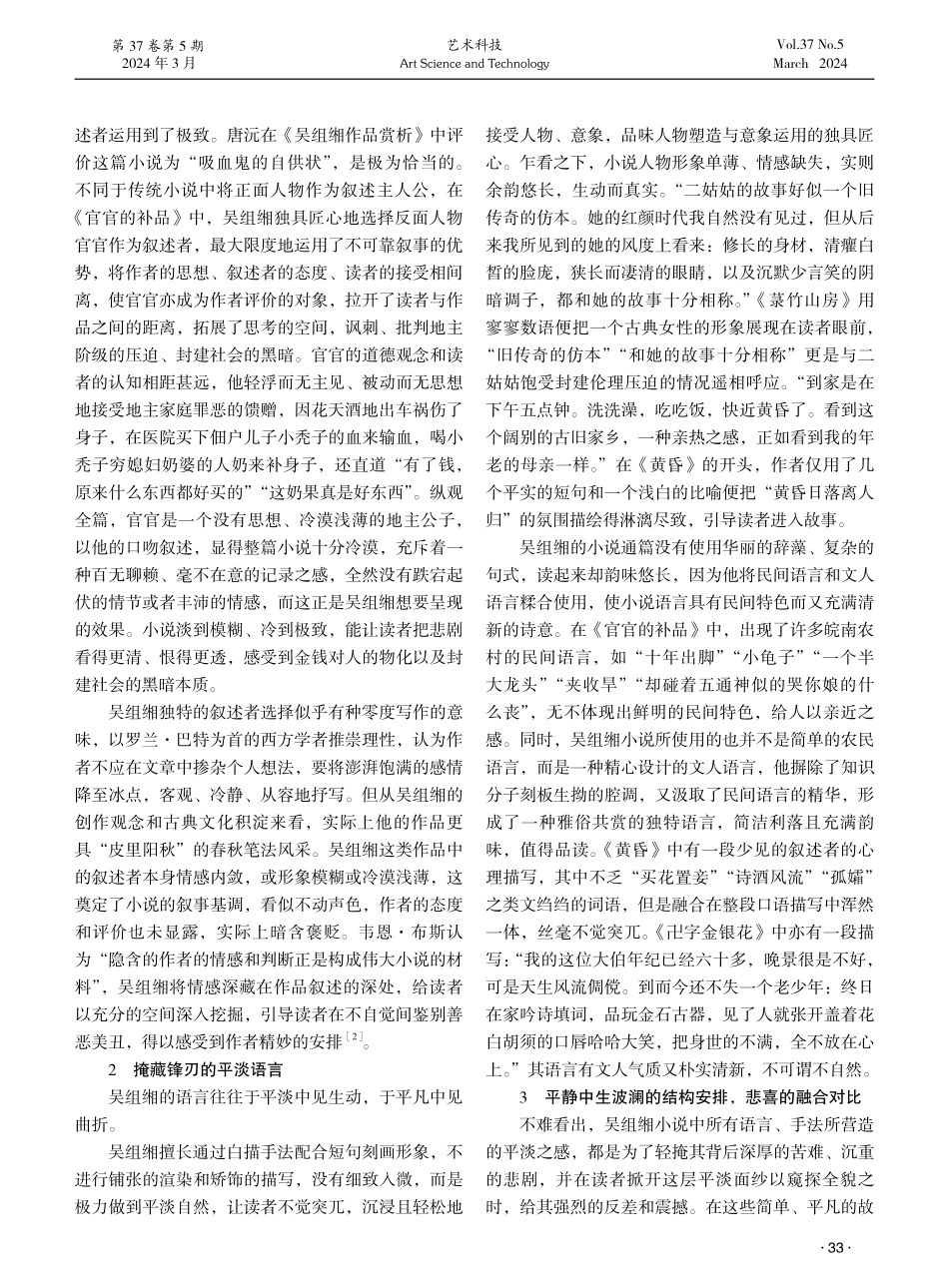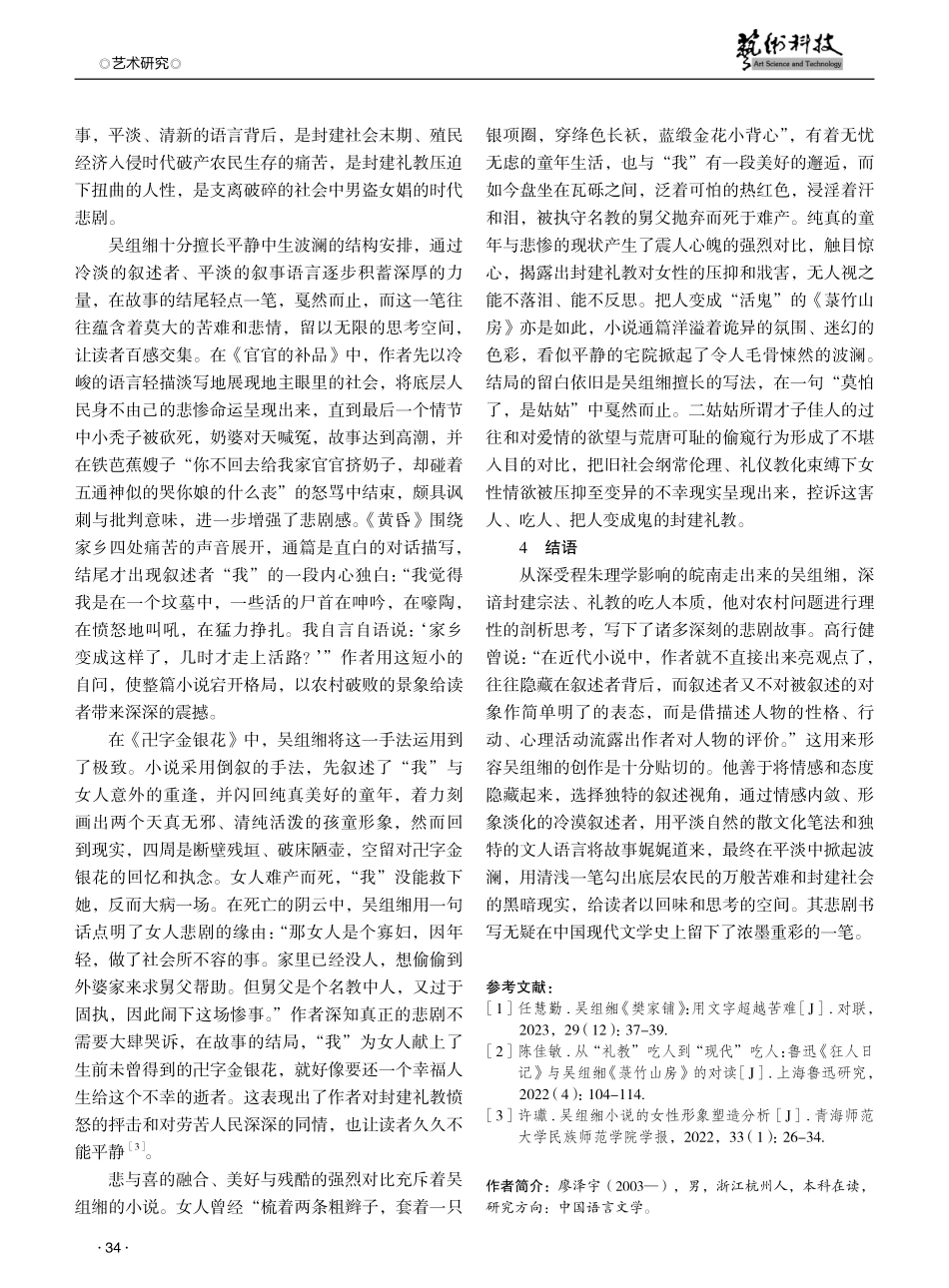·32·艺术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体中,吴组缃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存在,其创作既有乡土小说对乡土中国命运的怀恋与思考,又有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作家对农村现状的客观剖析与批判。作为一名学者作家,他用自己锐利的眼光洞察家乡皖南的世事变迁,并以成熟且独到的叙事手法和语言艺术呈现出地方风土的原生态,时而温情浮现,时而冷峻毒辣,有如含泪的微笑,在不动声色中展现对封建礼教和人的异化的抨击与批判。在其发表的小说作品中,悲剧是绝对的主题。吴组缃的《樊家铺》《天下太平》等作品,全面刻画了破产农民在生存的困境和社会的压迫中道德沦丧、家庭破败,最终挣扎着走向灭亡的过程。而本文着重探讨吴组缃的另一种悲剧叙事。在《卍字金银花》《菉竹山房》《官官的补品》《黄昏》等作品中,吴组缃通过散文化的笔法、情感收敛的叙述者,从营造或轻松平淡或充满乡土气息的氛围入手,和缓地展开故事情节,在收煞轻点一笔悲情,却又如针芒般不经意地刺入读者内心,勾起读者无尽的回味与叹惋。1…独特的叙述者选择吴组缃在小说中非常擅长使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一般而言,第一人称有限视角的叙述者可以作为故事的讲述者或参与者、主人公,能够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形成以人物为主导的叙述风格,给读者带来沉浸式的故事体验。同时,不可靠叙事也能使小说更耐人寻味、余韵悠长。吴组缃的第一人称小说不仅有此类优势,还因其自身的独特风格和学者气质展现出更具价值的特点。不同于许多第一人称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情感丰富、心理活动复杂的抒情主人公,吴组缃笔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体现出情感内敛、表态模糊、性格淡化的特点,也通常不以核心主人公的形态出现。在《黄昏》中,吴组缃舍弃了故事的前因后果,直接从“我”返回家乡开始叙述,围绕妻子、小玉和家乡人之间的对话展开故事。自始至终,叙述者“我”的职业、过往的生活、返乡的目的都未提及,除了“我”来自故事发生的村庄之外,作者未补充任何身份信息。因而在小说中,叙述者仅仅是故事发展的引线。因久未归乡,对家乡如今的人事不甚了解,“我”和读者一样,以陌生的认知进入叙事,通过“我”和妻子的问答、周遭家乡人发出的各种声音来逐步了解这个已然惨淡凋敝的村庄。不仅如此,在几乎由对话组成的文章中,除去结尾的一笔,“我”仅有12句对话,短至三五字,长不过七八字。“我”的情感是内敛的,形象是淡化的,读者对叙述者难以形成画像,因此读者会更关注其他人物对话中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