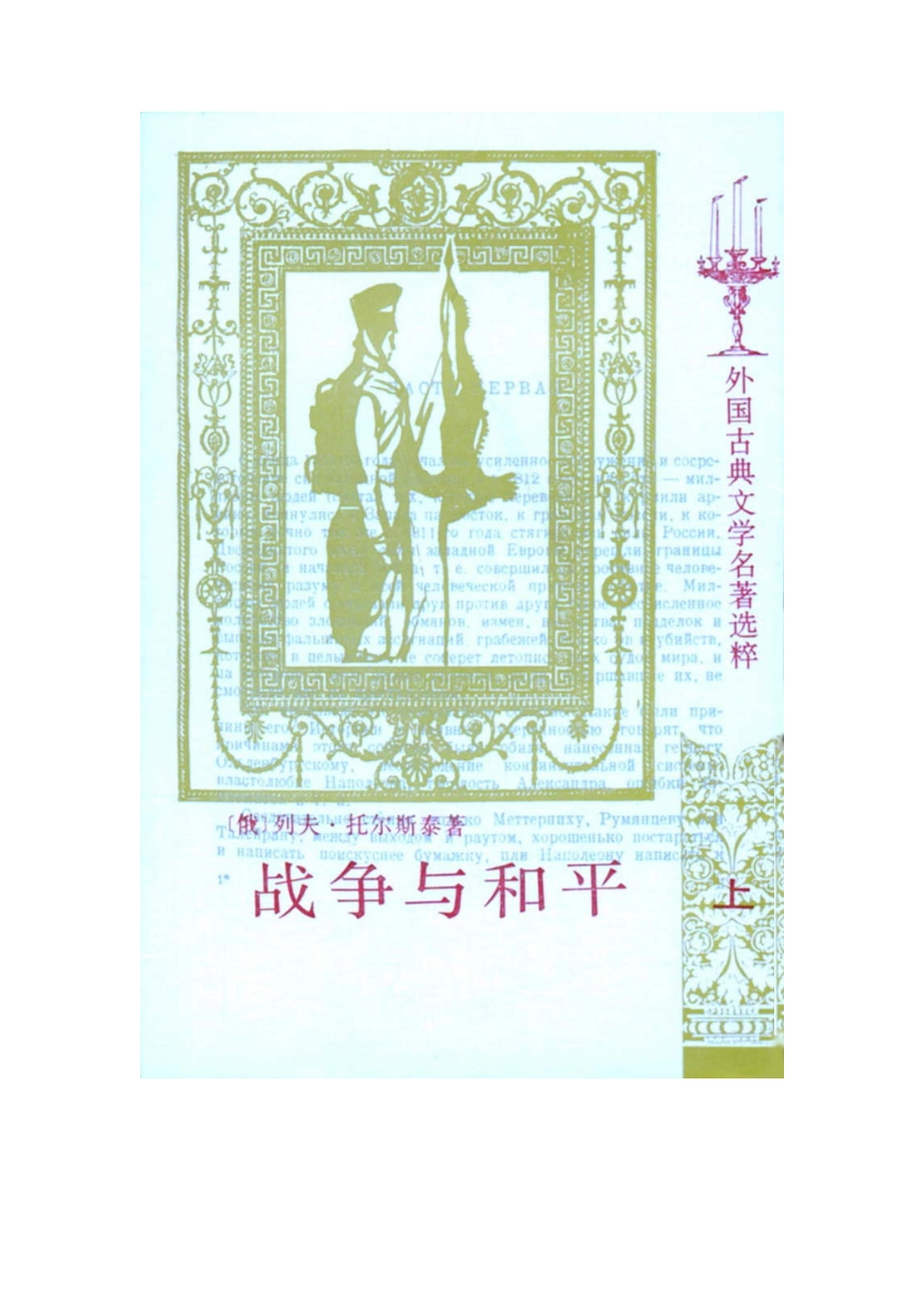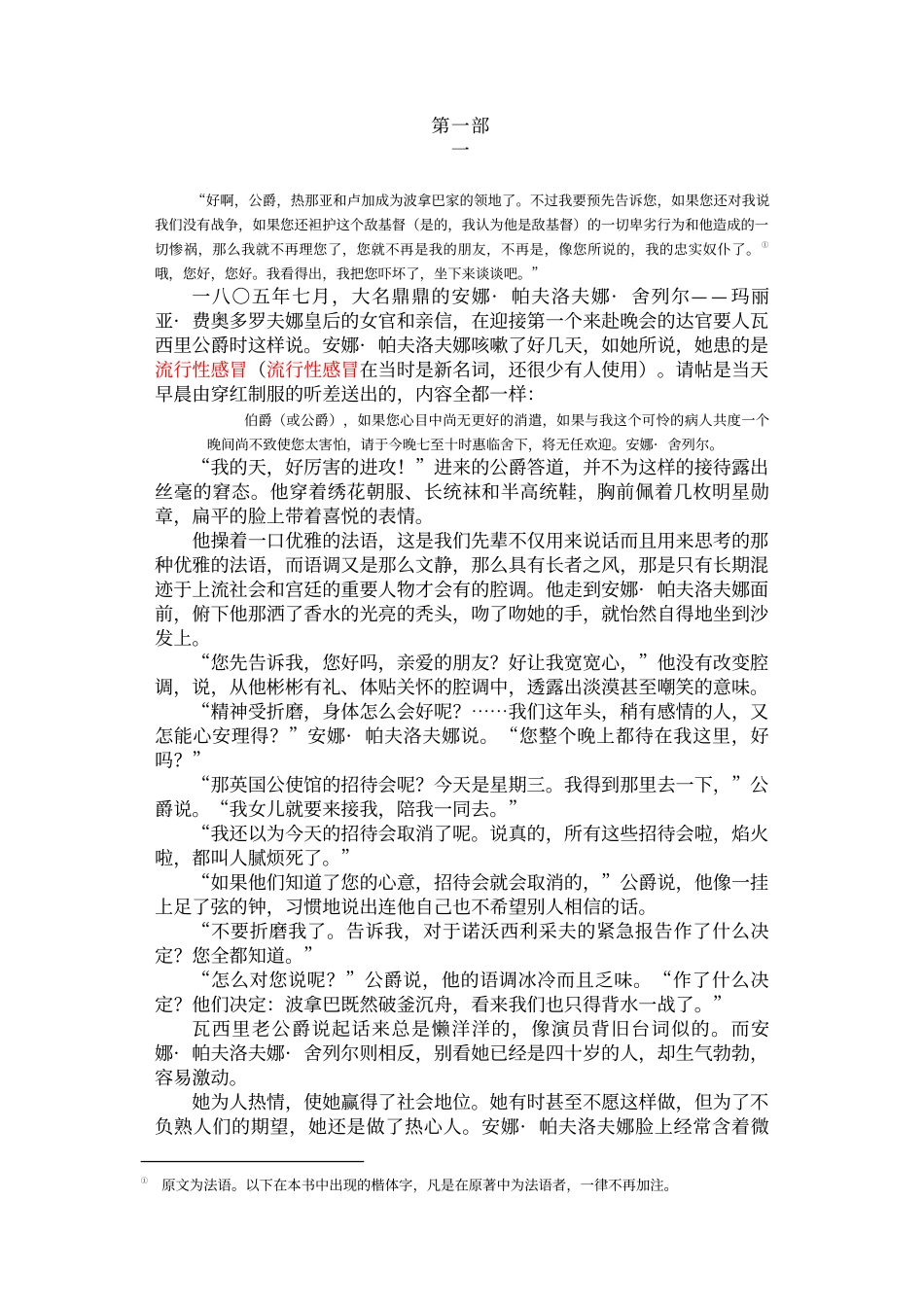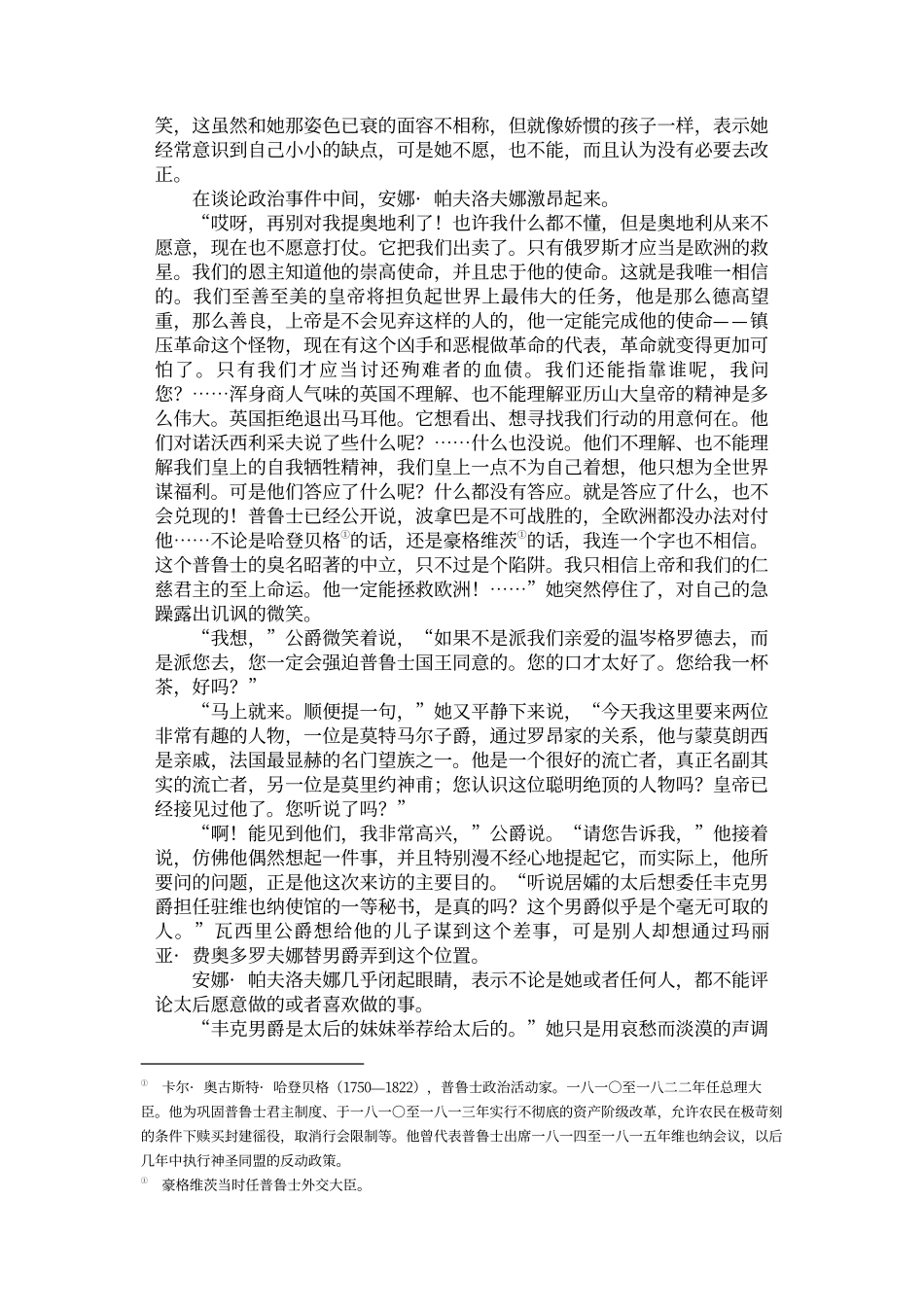第一部一“好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成为波拿巴家的领地了。不过我要预先告诉您,如果您还对我说我们没有战争,如果您还袒护这个敌基督(是的,我认为他是敌基督)的一切卑劣行为和他造成的一切惨祸,那么我就不再理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不再是,像您所说的,我的忠实奴仆了。①哦,您好,您好。我看得出,我把您吓坏了,坐下来谈谈吧。”一八○五年七月,大名鼎鼎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皇后的女官和亲信,在迎接第一个来赴晚会的达官要人瓦西里公爵时这样说。安娜·帕夫洛夫娜咳嗽了好几天,如她所说,她患的是流行性感冒(流行性感冒在当时是新名词,还很少有人使用)。请帖是当天早晨由穿红制服的听差送出的,内容全都一样:伯爵(或公爵),如果您心目中尚无更好的消遣,如果与我这个可怜的病人共度一个晚间尚不致使您太害怕,请于今晚七至十时惠临舍下,将无任欢迎。安娜·舍列尔。“我的天,好厉害的进攻!”进来的公爵答道,并不为这样的接待露出丝毫的窘态。他穿着绣花朝服、长统袜和半高统鞋,胸前佩着几枚明星勋章,扁平的脸上带着喜悦的表情。他操着一口优雅的法语,这是我们先辈不仅用来说话而且用来思考的那种优雅的法语,而语调又是那么文静,那么具有长者之风,那是只有长期混迹于上流社会和宫廷的重要人物才会有的腔调。他走到安娜·帕夫洛夫娜面前,俯下他那洒了香水的光亮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就怡然自得地坐到沙发上。“您先告诉我,您好吗,亲爱的朋友?好让我宽宽心,”他没有改变腔调,说,从他彬彬有礼、体贴关怀的腔调中,透露出淡漠甚至嘲笑的意味。“精神受折磨,身体怎么会好呢?⋯⋯我们这年头,稍有感情的人,又怎能心安理得?”安娜·帕夫洛夫娜说。“您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这里,好吗?”“那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呢?今天是星期三。我得到那里去一下,”公爵说。“我女儿就要来接我,陪我一同去。”“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说真的,所有这些招待会啦,焰火啦,都叫人腻烦死了。”“如果他们知道了您的心意,招待会就会取消的,”公爵说,他像一挂上足了弦的钟,习惯地说出连他自己也不希望别人相信的话。“不要折磨我了。告诉我,对于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报告作了什么决定?您全都知道。”“怎么对您说呢?”公爵说,他的语调冰冷而且乏味。“作了什么决定?他们决定:波拿巴既然破釜沉舟,看来我们也只得背水一战了。”瓦西里老公爵说起话来总是懒洋洋的,像演员背旧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