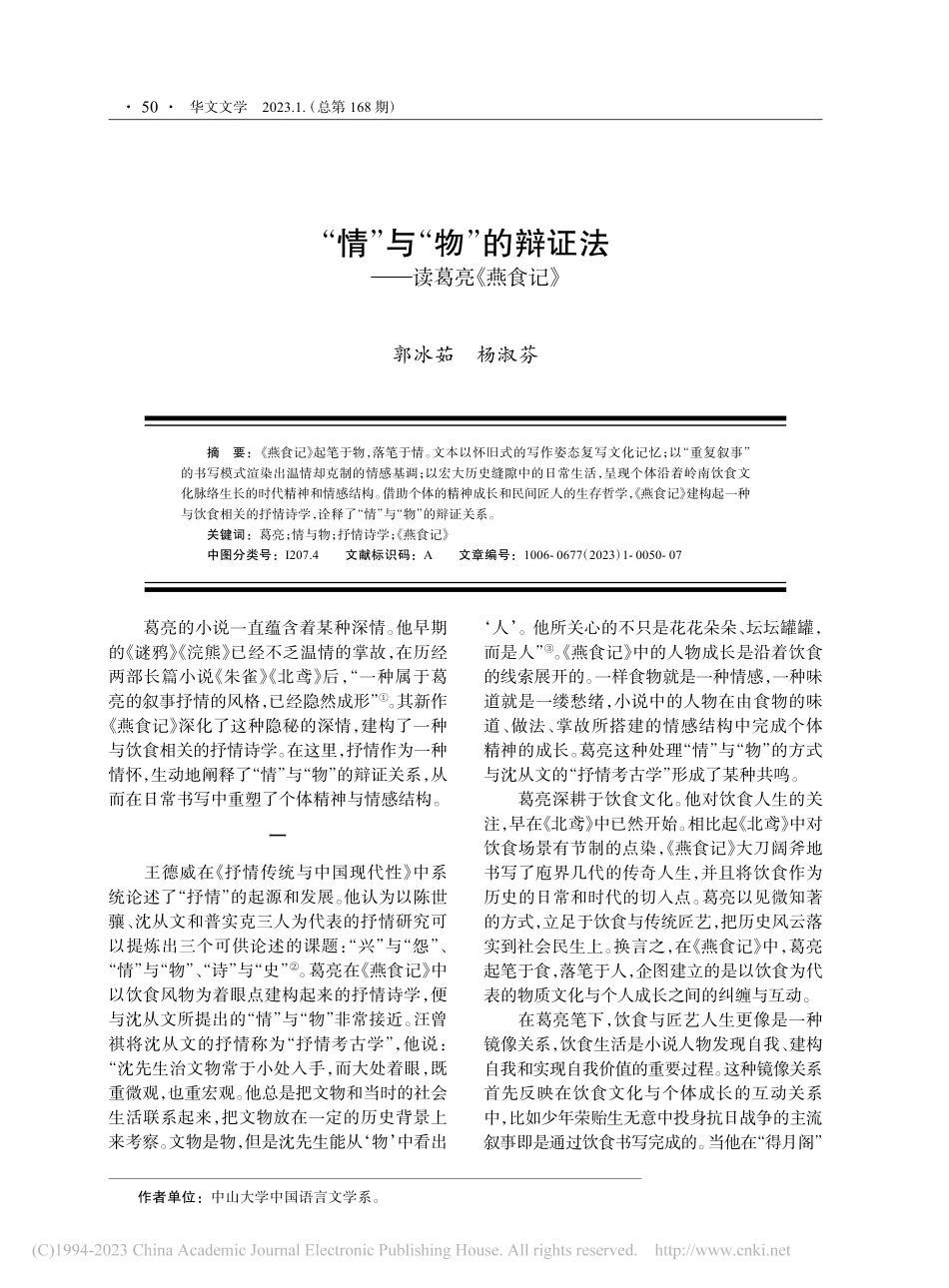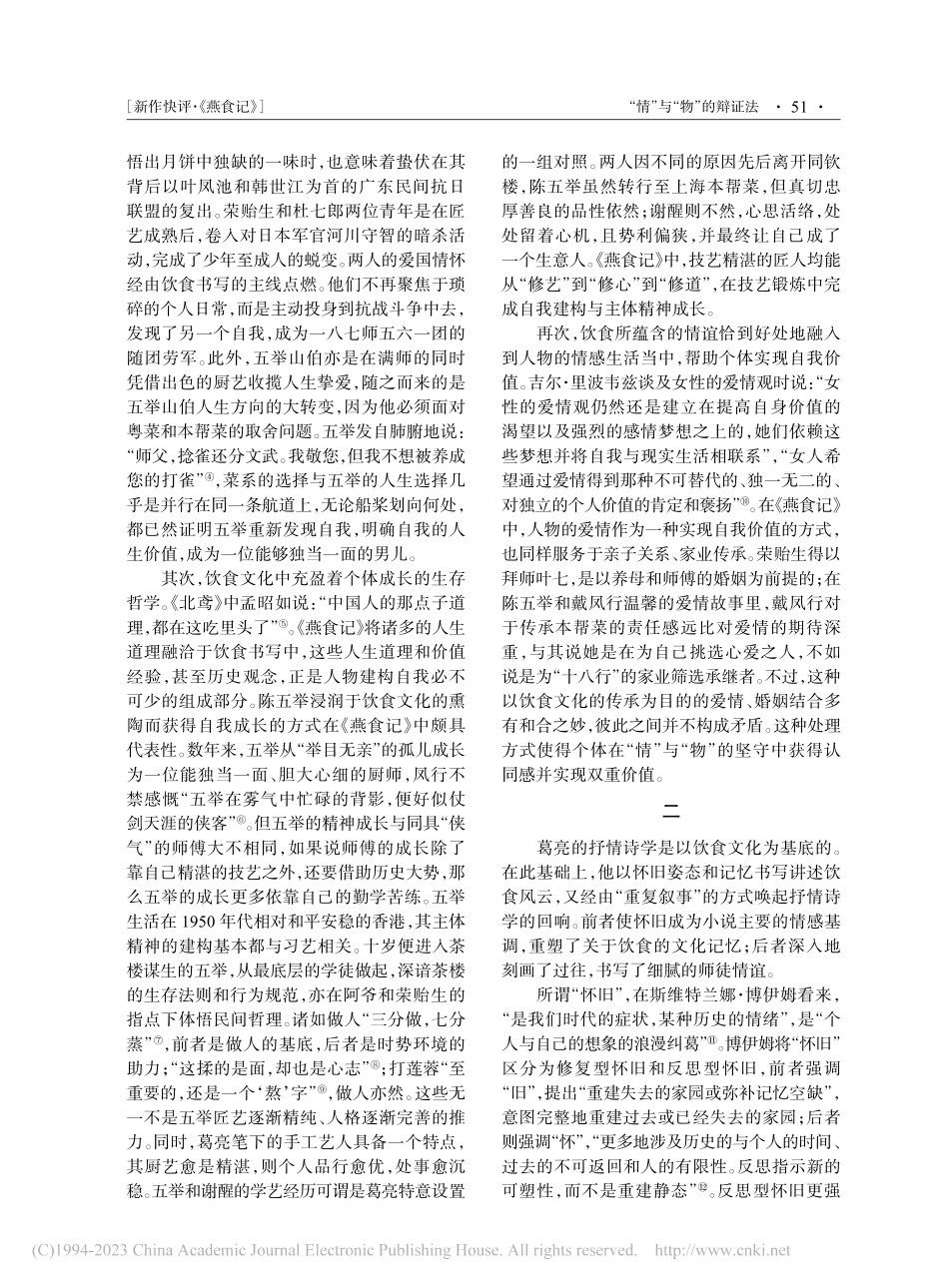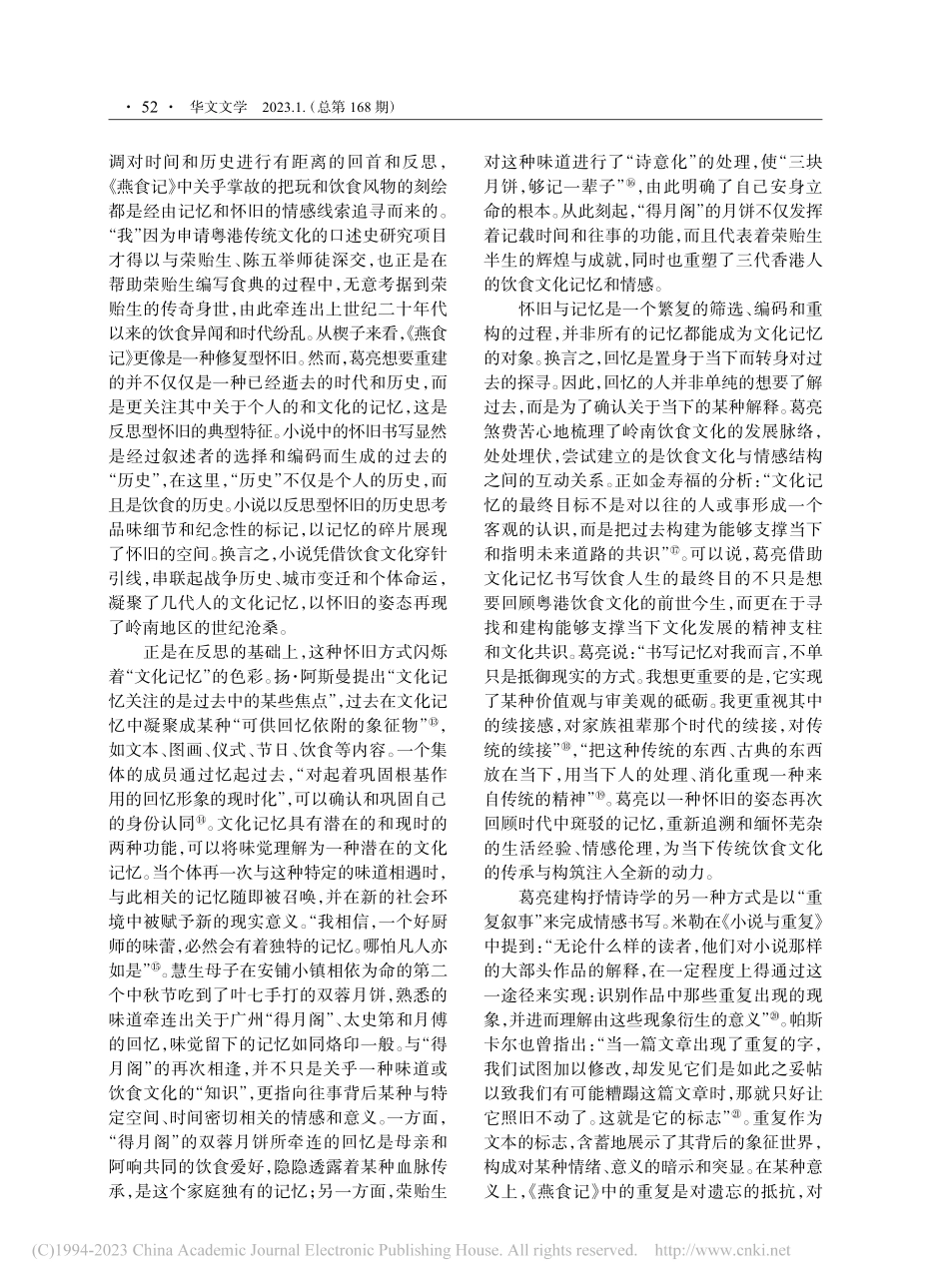华文文学2023.1.(总第168期)“情”与“物”的辩证法———读葛亮《燕食记》郭冰茹杨淑芬摘要:《燕食记》起笔于物,落笔于情。文本以怀旧式的写作姿态复写文化记忆;以“重复叙事”的书写模式渲染出温情却克制的情感基调;以宏大历史缝隙中的日常生活,呈现个体沿着岭南饮食文化脉络生长的时代精神和情感结构。借助个体的精神成长和民间匠人的生存哲学,《燕食记》建构起一种与饮食相关的抒情诗学,诠释了“情”与“物”的辩证关系。关键词:葛亮;情与物;抒情诗学;《燕食记》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23)1-0050-07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葛亮的小说一直蕴含着某种深情。他早期的《谜鸦》《浣熊》已经不乏温情的掌故,在历经两部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后,“一种属于葛亮的叙事抒情的风格,已经隐然成形”①。其新作《燕食记》深化了这种隐秘的深情,建构了一种与饮食相关的抒情诗学。在这里,抒情作为一种情怀,生动地阐释了“情”与“物”的辩证关系,从而在日常书写中重塑了个体精神与情感结构。一王德威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系统论述了“抒情”的起源和发展。他认为以陈世骧、沈从文和普实克三人为代表的抒情研究可以提炼出三个可供论述的课题:“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②。葛亮在《燕食记》中以饮食风物为着眼点建构起来的抒情诗学,便与沈从文所提出的“情”与“物”非常接近。汪曾祺将沈从文的抒情称为“抒情考古学”,他说:“沈先生治文物常于小处入手,而大处着眼,既重微观,也重宏观。他总是把文物和当时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把文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文物是物,但是沈先生能从‘物’中看出‘人’。他所关心的不只是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而是人”③。《燕食记》中的人物成长是沿着饮食的线索展开的。一样食物就是一种情感,一种味道就是一缕愁绪,小说中的人物在由食物的味道、做法、掌故所搭建的情感结构中完成个体精神的成长。葛亮这种处理“情”与“物”的方式与沈从文的“抒情考古学”形成了某种共鸣。葛亮深耕于饮食文化。他对饮食人生的关注,早在《北鸢》中已然开始。相比起《北鸢》中对饮食场景有节制的点染,《燕食记》大刀阔斧地书写了庖界几代的传奇人生,并且将饮食作为历史的日常和时代的切入点。葛亮以见微知著的方式,立足于饮食与传统匠艺,把历史风云落实到社会民生上。换言之,在《燕食记》中,葛亮起笔于食,落笔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