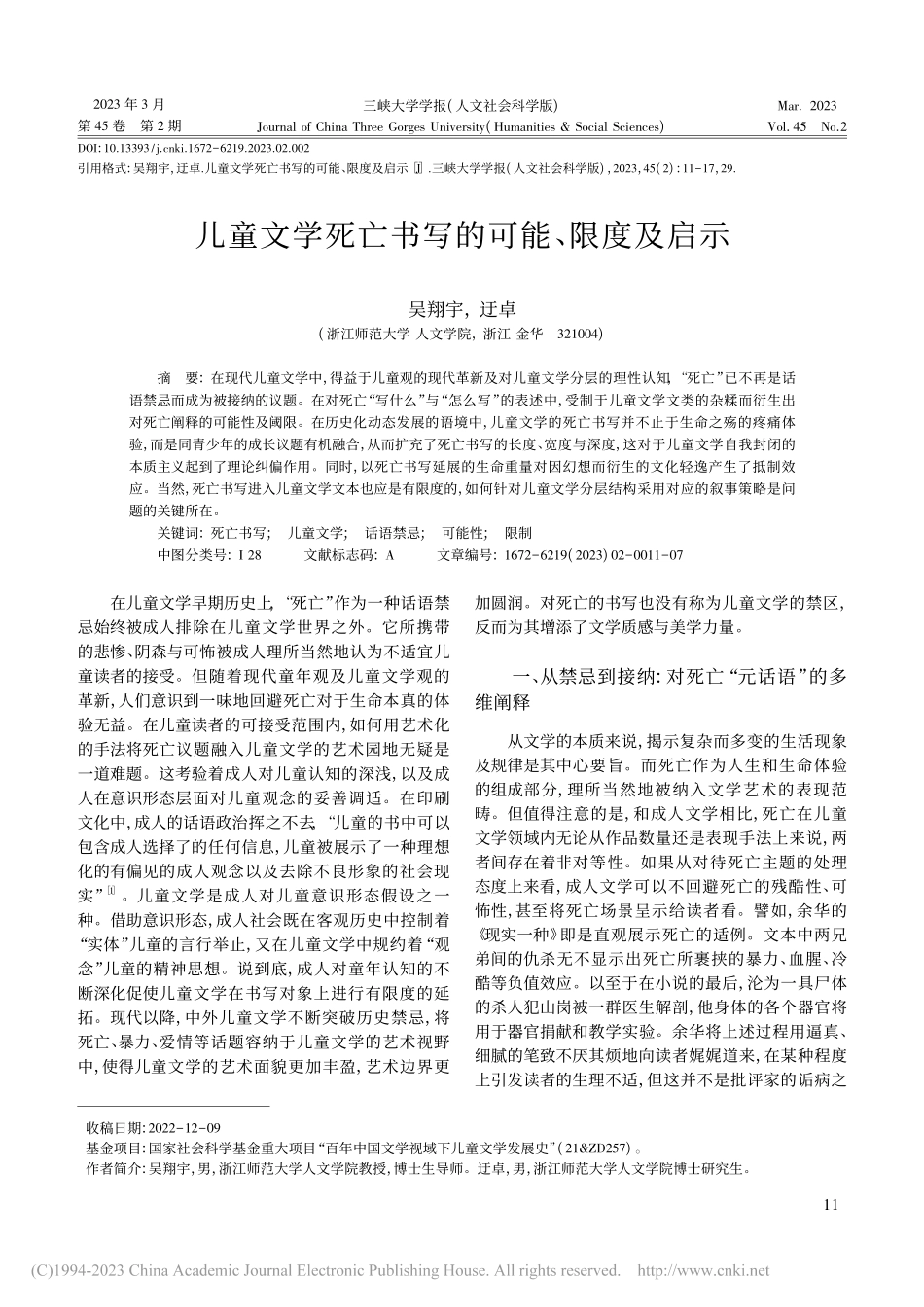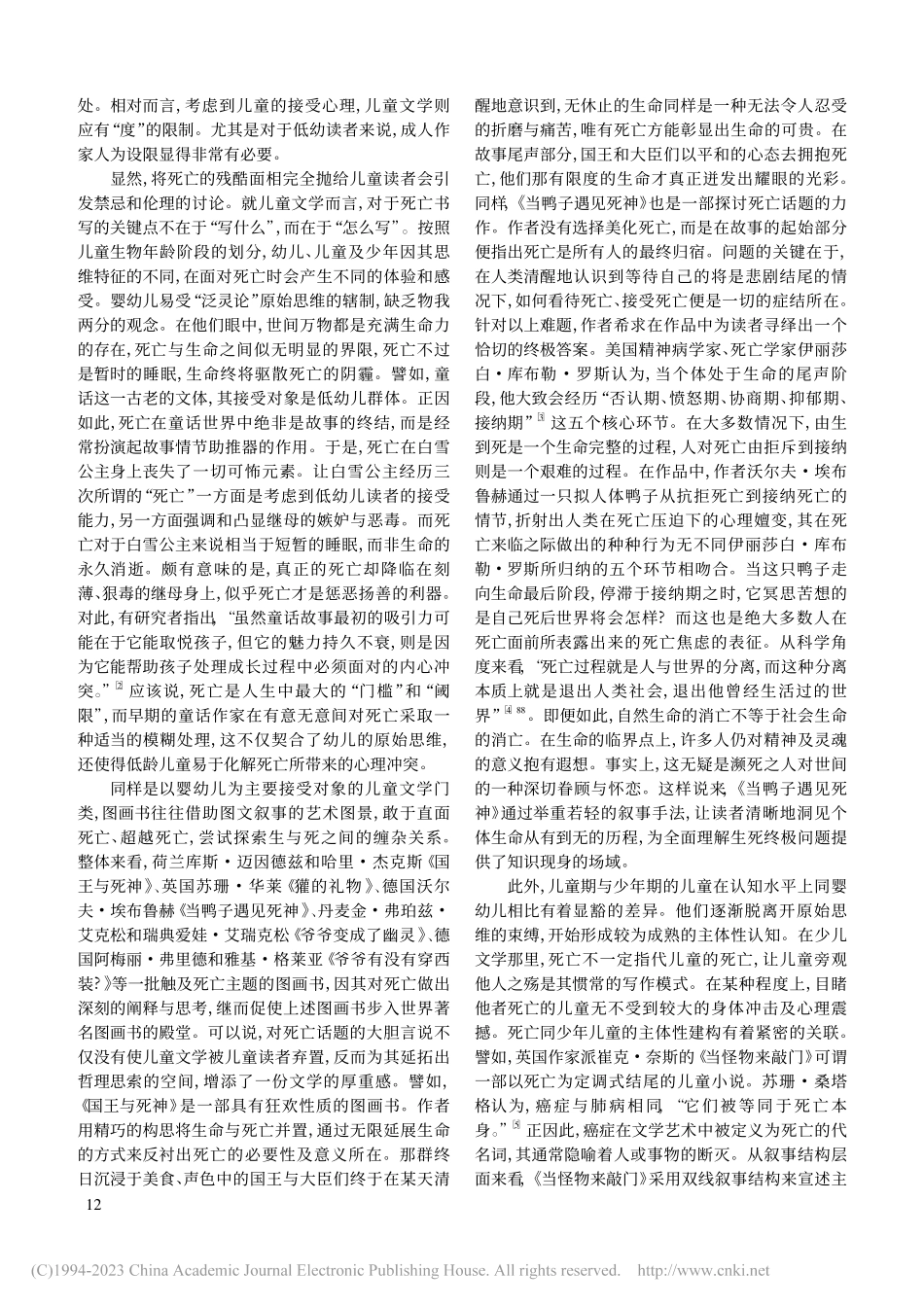收稿日期:2022-12-0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发展史”(21&ZD257)。作者简介:吴翔宇,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迂卓,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2023年3月第45卷第2期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ofChinaThreeGorgesUniversity(Humanities&SocialSciences)Mar.2023Vol.45No.2DOI:10.13393/j.cnki.1672-6219.2023.02.002引用格式:吴翔宇,迂卓.儿童文学死亡书写的可能、限度及启示[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5(2):11-17,29.儿童文学死亡书写的可能、限度及启示吴翔宇,迂卓(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摘要:在现代儿童文学中,得益于儿童观的现代革新及对儿童文学分层的理性认知,“死亡”已不再是话语禁忌而成为被接纳的议题。在对死亡“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表述中,受制于儿童文学文类的杂糅而衍生出对死亡阐释的可能性及阈限。在历史化动态发展的语境中,儿童文学的死亡书写并不止于生命之殇的疼痛体验,而是同青少年的成长议题有机融合,从而扩充了死亡书写的长度、宽度与深度,这对于儿童文学自我封闭的本质主义起到了理论纠偏作用。同时,以死亡书写延展的生命重量对因幻想而衍生的文化轻逸产生了抵制效应。当然,死亡书写进入儿童文学文本也应是有限度的,如何针对儿童文学分层结构采用对应的叙事策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词:死亡书写;儿童文学;话语禁忌;可能性;限制中图分类号:I2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6219(2023)02-0011-07在儿童文学早期历史上,“死亡”作为一种话语禁忌始终被成人排除在儿童文学世界之外。它所携带的悲惨、阴森与可怖被成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不适宜儿童读者的接受。但随着现代童年观及儿童文学观的革新,人们意识到一味地回避死亡对于生命本真的体验无益。在儿童读者的可接受范围内,如何用艺术化的手法将死亡议题融入儿童文学的艺术园地无疑是一道难题。这考验着成人对儿童认知的深浅,以及成人在意识形态层面对儿童观念的妥善调适。在印刷文化中,成人的话语政治挥之不去,“儿童的书中可以包含成人选择了的任何信息,儿童被展示了一种理想化的有偏见的成人观念以及去除不良形象的社会现实”[1]。儿童文学是成人对儿童意识形态假设之一种。借助意识形态,成人社会既在客观历史中控制着“实体”儿童的言行举止,又在儿童文学中规约着“观念”儿童的精神思想。说到底,成人对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