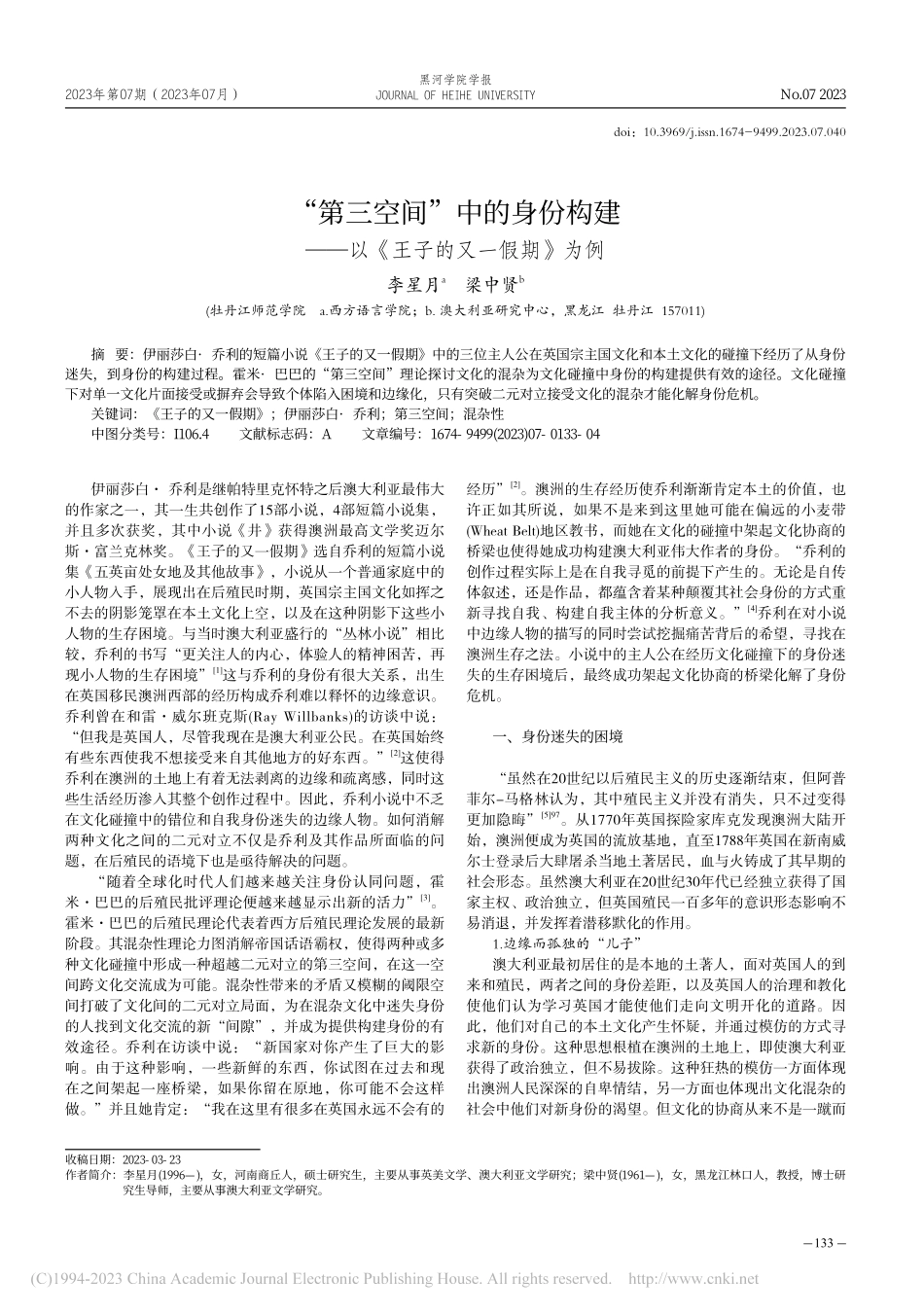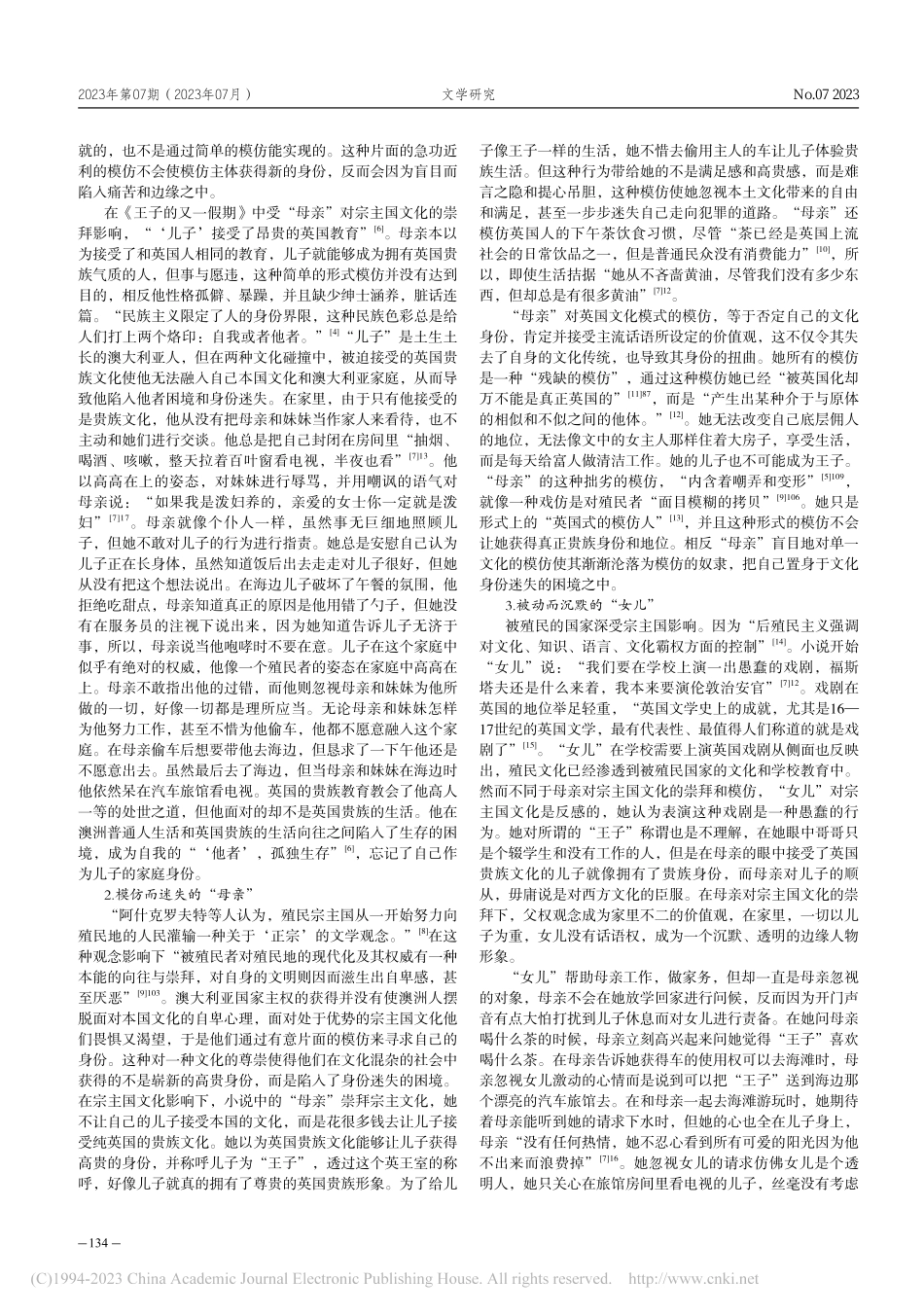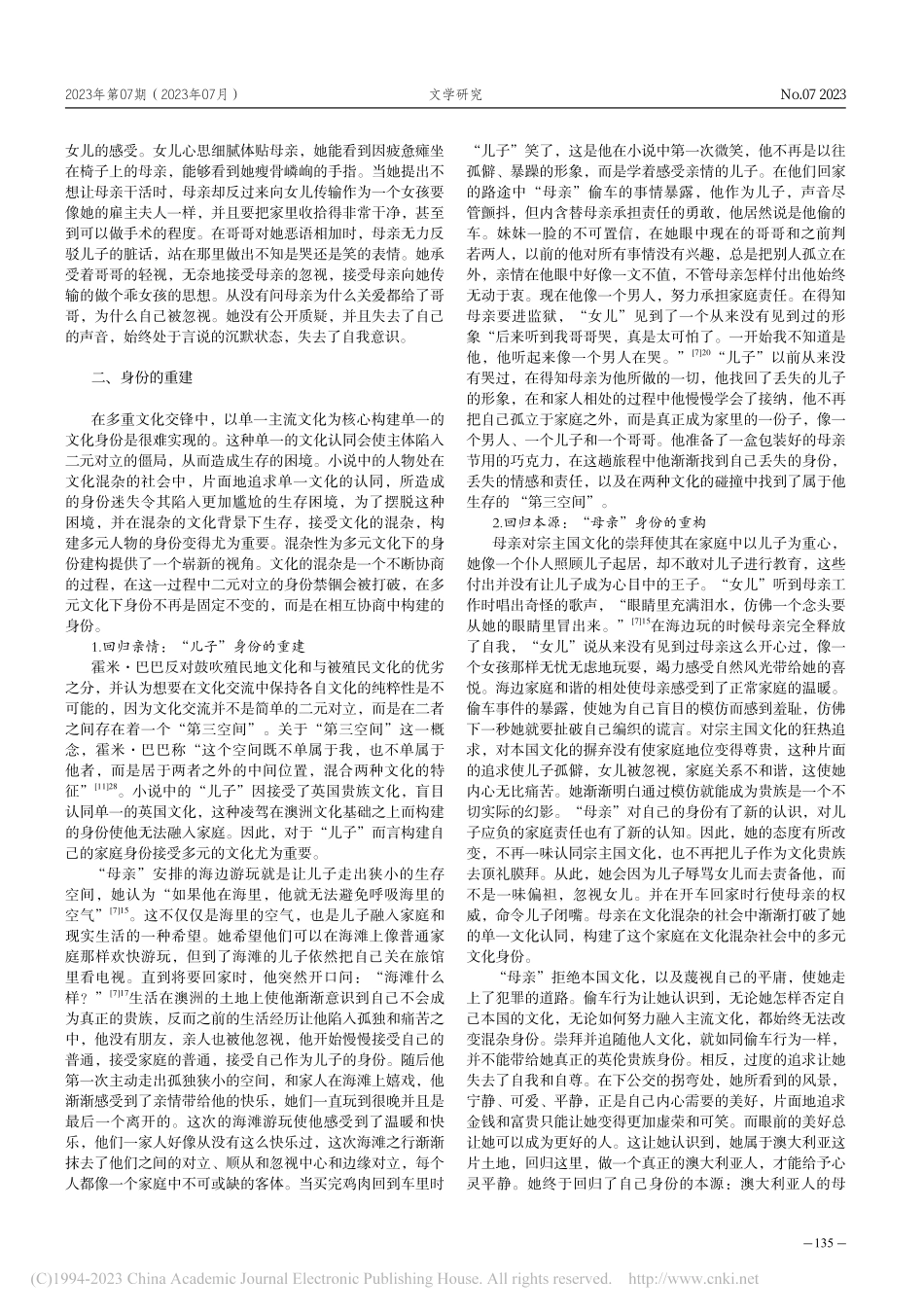2023年第07期(2023年07月)No.072023133伊丽莎白·乔利是继帕特里克怀特之后澳大利亚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其一生共创作了15部小说,4部短篇小说集,并且多次获奖,其中小说《井》获得澳洲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王子的又一假期》选自乔利的短篇小说集《五英亩处女地及其他故事》,小说从一个普通家庭中的小人物入手,展现出在后殖民时期,英国宗主国文化如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本土文化上空,以及在这种阴影下这些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当时澳大利亚盛行的“丛林小说”相比较,乔利的书写“更关注人的内心,体验人的精神困苦,再现小人物的生存困境”[1]这与乔利的身份有很大关系,出生在英国移民澳洲西部的经历构成乔利难以释怀的边缘意识。乔利曾在和雷·威尔班克斯(RayWillbanks)的访谈中说:“但我是英国人,尽管我现在是澳大利亚公民。在英国始终有些东西使我不想接受来自其他地方的好东西。”[2]这使得乔利在澳洲的土地上有着无法剥离的边缘和疏离感,同时这些生活经历渗入其整个创作过程中。因此,乔利小说中不乏在文化碰撞中的错位和自我身份迷失的边缘人物。如何消解两种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不仅是乔利及其作品所面临的问题,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全球化时代人们越来越关注身份认同问题,霍米·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便越来越显示出新的活力”[3]。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代表着西方后殖民理论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混杂性理论力图消解帝国话语霸权,使得两种或多种文化碰撞中形成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在这一空间跨文化交流成为可能。混杂性带来的矛盾又模糊的阈限空间打破了文化间的二元对立局面,为在混杂文化中迷失身份的人找到文化交流的新“间隙”,并成为提供构建身份的有效途径。乔利在访谈中说:“新国家对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一些新鲜的东西,你试图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果你留在原地,你可能不会这样做。”并且她肯定:“我在这里有很多在英国永远不会有的经历”[2]。澳洲的生存经历使乔利渐渐肯定本土的价值,也许正如其所说,如果不是来到这里她可能在偏远的小麦带(WheatBelt)地区教书,而她在文化的碰撞中架起文化协商的桥梁也使得她成功构建澳大利亚伟大作者的身份。“乔利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在自我寻觅的前提下产生的。无论是自传体叙述,还是作品,都蕴含着某种颠覆其社会身份的方式重新寻找自我、构建自我主体的分析意义。”[4]乔利在对小说中边缘人物的描...